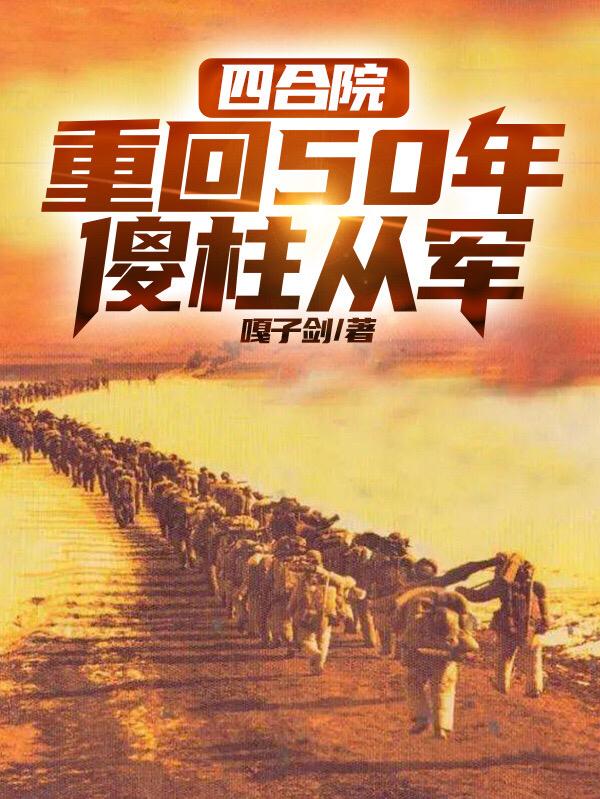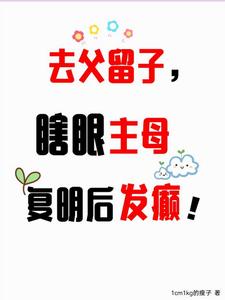第187章 设计图纸的陶片压印签名系统
纸上压出深浅恰好的纹路时,窗外的雨停了,夕阳正透过云层在图纸上投下斜斜的光带,像给那个印记镶了道金边。
“得有个定位系统。”赵环用圆规在图纸角落画了个十字,“每次压印都对准这个坐标,保证在规范允许的误差范围内。”他说着打开CAD,把郭静画的星芒图案转化成矢量图,“纹样用参数化设计,保留手工的随机感,但轮廓线精确到0.1毫米——就像你捏陶时,指尖的力度有潜意识在控制。”
郭静看着屏幕上逐渐成型的图案,星芒的每个角都带着细微的弧度变化,像被风吹得微微颤动。“你知道吗?窑里的温度场就像你的建筑日照分析图。”她忽然握住他握鼠标的手,让光标在星芒中心画了个极小的圆点,“这里留个凹坑,烧出来会积一点釉料,像你天窗设计里特意留的光斑落点。”
接下来的三天,他们的“签名系统”在理性与感性的拉扯中慢慢成型。赵环计算出最佳压印时机——陶片干燥至含水率12%时,既不会粘纸,又能留下足够深的纹理;郭静则调配出特制的陶土配方,加入少量瓷土增加硬度,又保留30%的粗砂颗粒,让印记边缘带着自然的颗粒感。
当第一批试制品出窑时,赵环正在开项目评审会。郭静把冷却后的陶片一个个摆在他的绘图桌上,每个都用软尺量过尺寸,在便签上标注着收缩率:“3号片收缩1.2%,最接近你的参数;7号片窑变出彩,星芒尖上有块金斑。”
他回来时,月光正透过天窗落在陶片上。拿起7号片时,指腹摸到星芒中心那个小圆坑,里面果然积着一点琥珀色的釉料,像郭静第一次吻他时,睫毛上沾的晨光。压印在最终版图纸上的那一刻,他忽然明白这个设计的真正意义:那些精确的坐标和参数,不过是为了让偶然的美好有处可寻,就像他用建筑规范框定空间,最终是为了让郭静指尖的温度,能在混凝土森林里找到恰好的落点。
甲方收到典藏版图纸那天,特意打来电话:“赵工,你的签名很特别,像把星星印在了纸上。”赵环看向正在给新陶片刻字的郭静,她正把他名字里的“环”字,刻成一圈围着星芒的弧线。
“是两个人的签名。”他轻声说,目光落在图纸上那个带着陶土温度的印记上——那里有建筑的理性骨架,有陶艺的感性肌理,更有两个生命在时光里,小心翼翼又无比笃定的共振。
雨又开始下了,这次绘图室里没有开灯。郭静把刚压好印的图纸举到窗前,雨水顺着玻璃蜿蜒流下,在灯光反射中,陶片压出的纹路仿佛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四合院:重回50年,傻柱从军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嘎子剑)的经典小说:《四合院:重回50年,傻柱从军》最新章节...
- 2306992字11-15
- 透视不赌石,你又在乱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迟暮流年)的经典小说:《透视不赌石,你又在乱看》最新章节全...
- 4147110字04-17
- 乖徒儿下山去吧,你师姐倾国倾城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玉扶风)的经典小说:《乖徒儿下山去吧,你师姐倾国倾城》最...
- 3142186字07-04
- 湖底(亲父女)
- 湖底(亲父女)最新章节由网友提供,《湖底(亲父女)》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是...
- 188604字07-21
- 哪怕背负百强企业,我也从不断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勇忘)的经典小说:《哪怕背负百强企业,我也从不断更》最新章...
- 2002353字05-12
- 去父留子,瞎眼主母复明后发癫!
- 去父留子,瞎眼主母复明后发癫!是由作者1ckg的瘦子著,免费提供去父留子,瞎眼主母复...
- 1981694字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