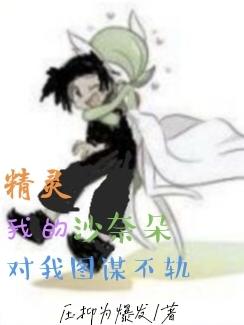第141章 商业项目招标书的陶艺装置提案
赵环的指尖在触控板上停顿了0.3秒,光标悬在“公共艺术装置方案”的标题栏上。办公室的落地窗外,初夏的阳光正以34度角斜切过CBD的玻璃幕墙,折射出的光斑恰好落在他摊开的招标书上——那是城东文化艺术中心的扩建项目,甲方要求在中庭设计一件既能呼应建筑肌理,又能传递“自然与人文共生”理念的装置作品。
他的钢笔在草稿纸边缘敲出规律的轻响,像是在为某个尚未成型的想法打节拍。建筑图纸上的中庭结构清晰得近乎冷酷:直径18米的圆形挑高空间,6根钢结构立柱呈六边形分布,玻璃穹顶的承重极限精确到每平方米230公斤。理性告诉他,这里需要一件形态稳定、材质耐久、符合消防规范的作品,但脑海深处却反复浮现另一幅画面——郭静工作室里,那些沾着指纹的陶坯在轮盘上旋转时,表面泛起的、如同呼吸般的微妙弧度。
手机在桌面震动了两下,是助理发来的公共艺术家推荐名单。赵环快速滑动屏幕,目光在“金属锻造”“数字投影”“石材雕刻”等关键词间掠过,直到看见某个名字旁括号里的“陶艺”二字,指尖忽然悬住了。
三天前在郭静的工作室,他曾见过她新作的一组“星轨陶片”。那些巴掌大的粗陶片上,她用指尖捏出深浅不一的凹痕,再以草木灰釉施彩,烧制后形成的裂纹像极了夜空中被拉长的星芒。当时郭静正蹲在窑边记录温度曲线,侧脸被火光映得发红:“你看这裂纹,永远猜不到它会往哪个方向走,就像泥土有自己的主意。”
赵环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玻璃上倒映出他衬衫口袋里露出的半截铅笔——那支笔的笔杆上,还留着上次在咖啡馆被郭静的咖啡杯蹭到的浅褐色渍痕。他想起她当时说“偶然的痕迹才最诚实”,忽然觉得,或许甲方要的“共生”,从来不是建筑对艺术的规训,而是两种不同语言的相互倾听。
拨通郭静电话时,他特意看了眼时间:下午四点十七分。这个时段她通常刚结束一轮烧制,应该在整理陶坯。听筒里传来轻微的沙沙声,像是她正用布擦拭手上的陶土,然后是她带着笑意的声音:“赵建筑师?你的设计图背面又写了什么诗?”
“这次不是诗。”赵环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公共艺术空间介入策略》,“有个项目想和你聊聊,关于陶艺装置。”
他听见那边的动作停了,几秒后,郭静的声音沉了些:“我从没做过商业项目。”
“我知道。”赵环翻开书,指尖划过某页关于“手工温度与工业空间对话”的论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627559字07-06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成为神豪后,只对大龄剩女感兴趣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飘泊的狼)的经典小说:《成为神豪后,只对大龄剩女感兴趣》最...
- 557418字06-29
- 星芒入怀:赵环与郭静的漫长共振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房三善)的经典小说:《星芒入怀:赵环与郭静的漫长共振》最...
- 410276字07-05
- 霁月难逢
- 534385字09-09
- 精灵我的沙奈朵对我图谋不轨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压抑为爆发)的经典小说:《精灵我的沙奈朵对我图谋不轨》最...
- 623603字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