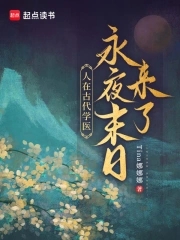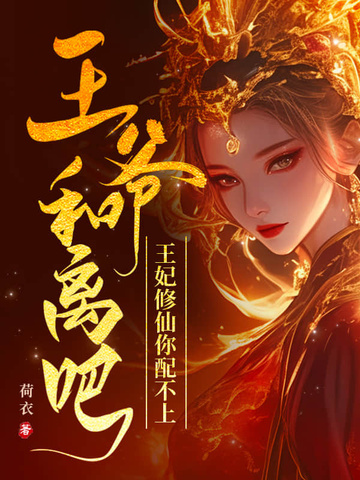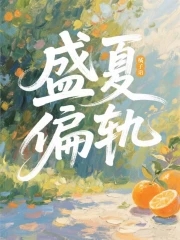第116章 他衬衫上的墨渍晕染成窑变纹路
陶艺都在跟材料对话。"他忽然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半度,"我用混凝土和钢材搭建空间时,总在找它们的'脾气',就像你摸陶土时知道该用几分力。"他顿了顿,看着她腕间的陶土屑,"上周我在老城区测绘,发现一堵明代砖墙的砖缝里嵌着陶片,那些碎片的弧度,跟你工作室里晾着的坯体转角一模一样。"
郭静的眼睛亮起来,像窑炉开窑时瞥见的第一缕金光。"你也注意到了?我前几天在碎陶堆里拼出个图案,后来发现竟跟你发在朋友圈的古桥拱券照片重合了三分之二。"她从帆布包里掏出本素描本,翻到某页,上面用铅笔勾勒着不规则的几何图形,边缘却晕染着水墨般的柔雾,"这是我用不同转速的陶轮甩出的泥痕,后来对照你的建筑剖面图,发现高转速形成的弧线恰好对应你说的'人流缓冲区域'。"
赵环接过素描本,指尖触到纸页上凹凸的笔触,那是郭静捏陶时用力留下的压痕。他忽然想起自己童年时用钢尺丈量老祠堂木柱的情景,那些木纹的走向,竟与郭静素描本上的泥痕有着相似的生命韵律。墨渍在衬衫上渐渐干透,形成的纹路越来越像某种密码,将他理性的建筑世界与她感性的陶土宇宙悄然连接。
"你看这墨渍。"郭静忽然指着他胸口,"深的地方像你设计图上的承重柱,浅的地方倒像我上窑前撒在坯体上的钴料——都是该控制却没控制住的部分,反而成了最生动的地方。"她的指尖在墨渍边缘轻轻画圈,"我师傅说过,陶土最讨厌被完全掌控,就像窑火总有自己的想法。"
赵环的心猛地一颤。他想起上个月被甲方否决的图书馆方案,只因他坚持在承重柱上留出雕刻凹槽,用来镶嵌老城区拆迁时收集的碎陶片。当时甲方拍着桌子说"建筑是理性的容器",而此刻郭静指尖的温度,却让他忽然明白,理性的极致或许正是对感性的臣服。
"我父亲是结构工程师。"他忽然开口,像是在揭开某个尘封的陶罐,"他总说建筑的灵魂在图纸的小数点后三位,直到我在他抽屉里发现未完成的自建房图纸——所有家具都按人体工程学摆放,却没有一扇窗朝向日出的方向。"墨渍的凉意透过衬衫贴在皮肤上,像块被窑火淬炼过的陶片,"后来我设计养老院时,故意把走廊弧度算成'60岁老人最佳日照接收角',被骂了整整三个小时。"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郭静静静地听着,从包里拿出个小巧的粗陶瓶,瓶身上有道自然形成的裂纹,却被金缮工艺修成了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人在古代学医,永夜末日来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Tina娜娜娜)的经典小说:《人在古代学医,永夜末日来了!》最...
- 320003字07-07
- 美漫里的恶魔果实
- 美漫里的恶魔果实章节目录,提供美漫里的恶魔果实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1873100字07-06
- 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箭心)的经典小说:《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最新章节全文...
- 525588字12-21
- 王爷和离吧,王妃修仙你配不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荷衣)的经典小说:《王爷和离吧,王妃修仙你配不上》最新章节...
- 326984字07-07
- 盛夏偏轨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橘子语.)的经典小说:《盛夏偏轨》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284892字07-07
- 高武:神魔纪元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毁灭尘埃)的经典小说:《高武:神魔纪元》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559910字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