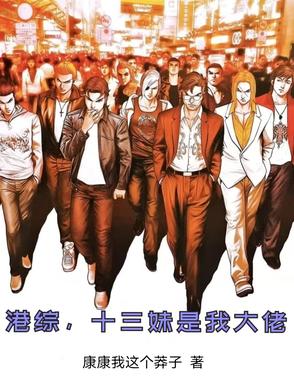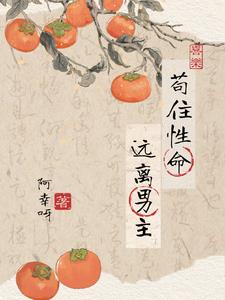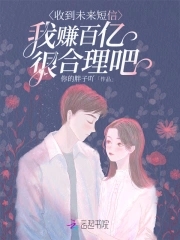第108章 感性土壤的震颤
室里弥漫着潮湿的陶土气息,混杂着釉料架上打翻的钴蓝粉末,在地板上形成一片星夜般的斑驳。
郭静扶着陶轮喘息,额发被汗水粘在额角。她低头看向掌心,那道螺旋状疤痕正渗出细密的汗珠,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心跳。地板上的泥痕还未干透,在灯光下泛着湿润的光泽,那道抛物线的尾端恰好落在窗台上一盆虎尾兰的叶片间,像一颗真正的星子坠入了绿色的春水。
她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跟着外婆去景德镇的老窑址拾柴。夕阳西下时,她看见窑坑底部有一块被烧成琉璃状的陶土,表面布满了放射状的裂纹,像极了夏夜突然划过的流星。外婆当时说:“这是火神的即兴创作,凡人学不来。”那时的她还不懂,为何完美的窑变总伴随着不可预测的失控。
陶轮的余震还在工作室里回荡。郭静走到落地窗前,指尖轻轻触碰那道泥痕。冰凉的玻璃与温热的陶土痕迹形成奇妙的温差,让她想起去年冬天在故宫看到的雪景——白雪覆盖的琉璃瓦上,落着几片未化的秋叶,那是时光在秩序中留下的意外褶皱。
“或许失控才是泥土的真相。”她喃喃道,蹲下身观察那团变形的泥坯。原本想做的花瓶已彻底走样,却在底部形成一个凹陷的弧面,像被星子砸出的小湖。弧面边缘有几道细长的裂纹,从中心向外辐射,恰似她童年见过的那片窑坑底部的琉璃陶土。
工作室的角落堆着她近半年的失败作品。有歪脖子的茶杯,有釉色斑驳的花瓶,还有一整箱因窑变失败而碎裂的陶片。此刻她忽然觉得,这些“失败”或许从未真正失败——那只歪脖子茶杯的弧度,像极了老城区巷口那棵斜长的石榴树;那片斑驳的釉色,分明是去年深秋暴雨初晴时的天空;而那些碎裂的陶片,每一块的断口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熔痕,如同不同星轨的截面。
墙上的《窑火时序图》又被风吹动,金粉描出的凌晨三点拐点在光影中闪烁。郭静起身走到釉料架前,捡起那只被泥点砸中的钴蓝瓶。瓶身上的泥点已有些干涸,形成不规则的星芒形状,让她想起巴黎留学时在蓬皮杜美术馆看到的某件装置艺术——金属丝缠绕的星图,每一颗“星子”都是用不同年代的碎瓷片拼成。
“原来如此。”她忽然轻笑出声,声音在空旷的工作室里显得有些突兀。她终于明白,为何每次揉泥时,老师傅总说“要像哄孩子”——陶土不是被动的材料,而是有记忆、有情绪的生命体,当它感受到掌心的焦虑或执念时,便会用失控来提醒人类:理性的掌控之外,还有更广阔的感性疆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港综,十三妹是我大佬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康康我这个莽子)的经典小说:《港综,十三妹是我大佬》最新章...
- 660460字05-07
- 苟住性命,远离男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阿幸呀)的经典小说:《苟住性命,远离男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668521字04-15
- 表姑娘定亲后,清冷探花黑化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我不困顿)的经典小说:《表姑娘定亲后,清冷探花黑化了》最新...
- 417831字09-10
- 快穿之路人甲的爱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红叶沫沫)的经典小说:《快穿之路人甲的爱情》最新章节全文...
- 3609065字05-30
- 收到未来短信,我赚百亿很合理吧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你的胖子吖)的经典小说:《收到未来短信,我赚百亿很合理吧》...
- 2572334字03-02
- 四合院:60年代一厨子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一只胖胖的猪)的经典小说:《四合院:60年代一厨子》最新章...
- 1111470字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