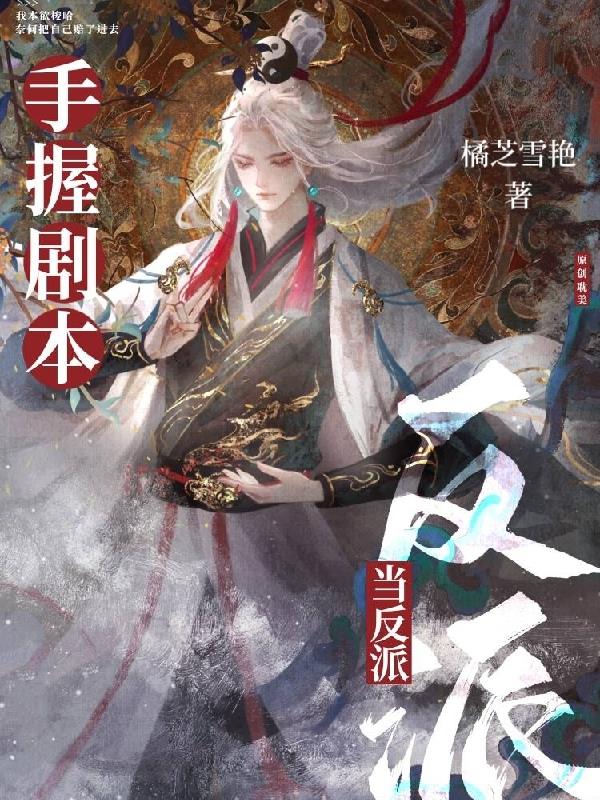第105章 命运的和弦准备
是时光的容器,每个指纹都是灵魂与泥土的契约。”
他忽然想起去年在老城区测绘时,从砖墙缝里捡到的半片宋代陶瓦,上面的水波纹路与这杂志上郭静作品的肌理惊人相似。那时他把陶瓦放在工作室的窗台上,此刻月光正透过玻璃照在瓦面上,那些千年以前的指痕仿佛在微光中重新苏醒。
电脑屏幕突然暗下来,屏保跳出他去年在希腊拍的帕特农神庙照片。那些历经风雨的石柱沟壑里,他曾用指尖丈量过古希腊人凿刻的弧度,发现每道凹槽的深度都与阳光照射角度形成精密的数学关系——理性与感性在石头里沉睡了两千年,直到某个游客的触碰才苏醒片刻。
“郭静……”他再次默念这个名字,打开浏览器搜索她的工作室地址。地图显示位于城郊的陶艺村,距离他设计的美术馆工地恰好七公里。这个数字让他想起建筑里的“黄金分割比”,某种隐秘的秩序感顺着脊椎爬上后颈。
窗外的天色开始泛白,第一缕晨光斜切进工作室,照亮了模型台上未完成的美术馆缩微模型。穹顶的镂空结构在光线下投下星点状的阴影,落在台面上的陶瓦残片上,那些水波纹路与阴影重叠时,竟形成了酷似郭静杂志照片里陶罐上的星图。
他拿出手机,找到陈总的微信对话框,指尖悬在键盘上方良久,最终只回了两个字:“好的。”
放下手机,他走到窗边推开百叶窗。春晨的风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涌进来,比昨夜的风多了几分暖意。远处的陶艺村方向,有只鸟雀正穿过薄雾,翅膀划过的弧线让他下意识想起郭静专访里提到的“陶轮转速与心跳的共振”。
工作室的时钟指向四点十五分,他重新坐回设计桌前,没有继续修改穹顶图纸,而是拿出空白速写本,用钢笔在扉页轻轻勾勒。笔尖先画出一道流畅的抛物线,像星子坠落的轨迹,然后在弧线下方点出数枚星芒,最后在落点处画了个不规则的椭圆——那是陶轮的轮廓。
画到这里,他忽然停笔,想起父亲曾说过的话:“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每个线条都该有数学的格律。”但此刻速写本上的线条却违背了所有力学公式,星轨的弧度带着某种非理性的柔美,仿佛下一秒就会从纸页上挣脱,坠入某个等待已久的容器。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他翻开速写本的前页,那里贴着张泛黄的便签,是多年前在巴黎建筑展上捡到的,上面用中文写着:“光该有形状,如同灵魂该有居所。”当时他以为是某个游客的随手涂鸦,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超高智商五人帮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绛云漫卷)的经典小说:《超高智商五人帮》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476074字09-28
- 惊!万人迷反派竟是龙傲天他老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橘芝雪艳)的经典小说:《惊!万人迷反派竟是龙傲天他老婆》...
- 1365845字12-23
- 疯魔
- 疯魔最新章节由网友提供,《疯魔》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是一本情节与文笔俱佳的...
- 41148字10-11
- 农家小奶包:又萌又气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渔火不是火)的经典小说:《农家小奶包:又萌又气人》最新章...
- 1652055字10-24
- 超神学院:极境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香菜巧克力)的经典小说:《超神学院:极境》最新章节全文阅...
- 593080字10-30
- 重生回来后带着空间回家悠闲种地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苦苦的薄荷糖)的经典小说:《重生回来后带着空间回家悠闲种...
- 1216191字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