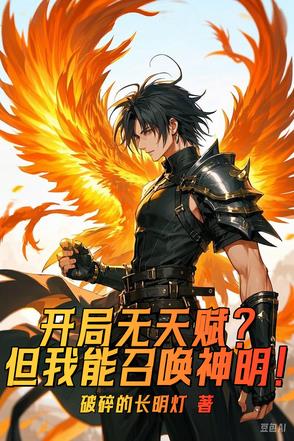第25章 雪夜的古建筑测绘
零下十度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古戏台的飞檐,赵环裹紧了羽绒服,睫毛上已经结了一层白霜。三脚架上的激光测距仪在雪光中闪着幽蓝的光,父亲递过来的热可可早已凉透,杯壁上凝着的水珠冻成了细小的冰晶。
“檐角走兽的位置再测一遍,误差不能超过五毫米。”父亲的声音透过厚厚的围巾传出来,带着呵气成雾的白汽。赵环点点头,手指在低温下冻得发紫,按在测距仪按钮上时,几乎感觉不到触感。古戏台的藻井在雪夜里沉默着,木雕的八仙过海图案被积雪覆盖,只露出模糊的轮廓,像一幅被时光晕染的水墨画。
这是赵环第三次跟着父亲来测绘这座清代古戏台。前两次分别是在盛夏和深秋,而这次的雪夜测绘,父亲说是为了记录建筑在极端温度下的形变数据。雪粒子打在青瓦上沙沙作响,远处的村庄传来几声犬吠,更衬得古戏台像一艘搁浅在雪原上的方舟。
“你看这戗脊的弧度,”父亲用红色激光笔指向檐角,“雪的堆积会改变它的受力分布,传统匠人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戗脊的曲线刚好能引导积雪滑落。”赵环顺着激光的方向望去,只见雪粒在戗脊上形成一条流畅的弧线,像少女披散的长发,而檐角的走兽雕塑——一只昂首的麒麟,正衔着那缕“发丝”,在夜空中定格成一个优美的姿势。
他蹲下身,用冻得僵硬的手指拂去台基上的积雪。青砖缝隙里嵌着冰棱,在手电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忽然,他发现一块方砖上刻着模糊的年号,“乾隆二十三年”几个字被风化得只剩下轮廓,却像某种神秘的密码,在雪夜里发出无声的召唤。
“爸,你说古人为什么要在戏台上刻这些年号?”赵环呵着白气问,哈出的水汽瞬间在眉毛上结成冰晶。父亲正在笔记本上记录数据,闻言头也不抬地说:“为了留下痕迹,证明他们存在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每一道刻痕都是时间的指纹。”
赵环站起身,抬头望向戏台的匾额。“古乐流芳”四个大字被积雪覆盖了一半,露出的“古”字右上角,有一道细微的裂缝,像一滴凝固的泪痕。他想起白天在县志上读到的记载:这座戏台曾在道光年间经历过一场大火,后被乡绅集资重建。那道裂缝,会不会就是大火留下的伤疤?
雪越下越大,鹅毛般的雪花在测绘灯的光束里狂舞,像无数飞蛾扑向光明。赵环负责测量戏台柱子的垂直度,激光束打在朱红的柱身上,留下一个微小的红点。他忽然注意到,柱子上有几处不规则的凹痕,像是被某种利器反复敲击过。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分手当天,财阀继承人倒贴上门
- 分手当天,财阀继承人倒贴上门是由作者黑森林西米露著,免费提供分手当天,财阀继承人...
- 1003208字03-15
- 东京喰种:噬魂搜查官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枫叶飘飞雪)的经典小说:《东京喰种:噬魂搜查官》最新章节...
- 666273字06-28
- 龙族:我的老爹是昂热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阳光老豆)的经典小说:《龙族:我的老爹是昂热》最新章节全...
- 481643字06-26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627559字07-06
- 都市逍遥小神医
- 都市逍遥小神医是由作者花小楼著,免费提供都市逍遥小神医最新清爽干净的文字章节在...
- 726505字12-21
- 开局无天赋?但我能召唤神明!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破碎的长明灯)的经典小说:《开局无天赋?但我能召唤神明!...
- 771914字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