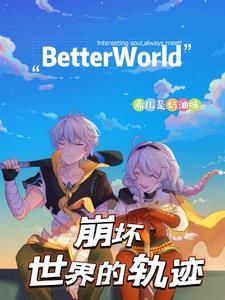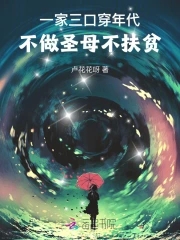第22章 母亲的陶碗经济学
”母亲把算盘拍在郭静面前时,她正在美院读大二。笔记本上画满了变形的月亮,而母亲用红铅笔在空白处列公式:“釉料成本÷烧制成功率=单件损耗”。郭静赌气用陶土捏了只方碗,母亲抄起篾条就打:“方碗盛饭要撒!你外婆教我时说,陶土是泥巴,更是肚皮,别尽整些天上的星星!”
篾条落在手背的瞬间,郭静想起七岁那年窑炉炸裂的陶碗。母亲当时正用布巾擦着合格品,火星溅到她围裙上烧出个洞,她却头也不抬:“碎了就碎了,再和三斤泥。”可郭静分明看见,母亲半夜偷偷把那些碎陶片埋在老槐树底下,月光照着她的背影,像给碎陶片镀了层金边。
笔记的第37页夹着张泛黄的糖纸。郭静对着光看,糖纸背面用指甲刻着朵未开的兰花——那是母亲年轻时的签名样式。旁边是密密麻麻的数字:“粗陶碗成本0.8元,售价1.2元,利润0.4元。若加刻花,耗时增加两刻,售价可提0.3元,但废品率上升5%。”最后一行字被指腹摩挲得模糊:“刻兰花的碗,总被第一个买走。”
那年冬天,母亲接了笔给茶馆做茶具的生意。郭静放假回家,看见她在昏暗的台灯下刻花,青竹纹在白釉上一点点显形。“茶馆老板说要素雅。”母亲头也不抬,刻刀在碗沿划出细响,“你外婆以前最会刻这种纹,说竹子是泥里长出来的骨头。”
郭静伸手去拿陶碗,却碰倒了母亲的药瓶。降压药撒在刻了一半的竹节上,像落了场不合时宜的雪。母亲慌忙去捡,银发从鬓角滑下来,沾到碗底未干的釉料上。“妈,我来刻吧。”郭静接过刻刀,却发现母亲的指尖在发抖——那些年拉坯留下的老茧,如今成了关节炎的温床。
“你那是搞艺术的手。”母亲抽回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我这双手知道泥性,刻坏了三十个,这是第三十一个。”郭静这才注意到脚边的废料桶,里面堆着三十只带竹节的碎碗,每道裂纹都像极了母亲手背的青筋。
茶馆老板来验货时,母亲把刻着兰花的样品藏在身后。“全要青竹纹。”老板吐着烟圈,“兰花娇气,喝茶的人嫌晦气。”母亲没说话,等老板走后,才把那只兰花碗塞进郭静行李:“路上喝水用,别让人看见。”
现在,郭静蹲在工作室的泥料堆前,手里捏着块陈腐三年的紫泥。母亲的笔记摊在脚边,第56页记着“星子釉配方”:“钴料三钱,金砂七分,需在窑温1280度时投柴三次,如向夜空抛洒星子。”旁边用红笔打了叉:“此为虚耗,务实者不为。”
本小章还未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厨子穿越傻柱之生五娃三子两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公子下班了)的经典小说:《厨子穿越傻柱之生五娃三子两女》...
- 452867字05-05
- 追燕
- 505604字09-10
- 苏家嫡女强势归来
- 671742字07-30
- 崩坏:我的姐姐是草履虫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希儿是奶油味)的经典小说:《崩坏:我的姐姐是草履虫》最新...
- 1930980字07-26
- 脚下恋人(BDSM)
- 脚下恋人(BDSM)章节目录,提供脚下恋人(BDSM)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105012字10-21
- 一家三口穿年代,不做圣母不扶贫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卢花花呀)的经典小说:《一家三口穿年代,不做圣母不扶贫》最...
- 1047741字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