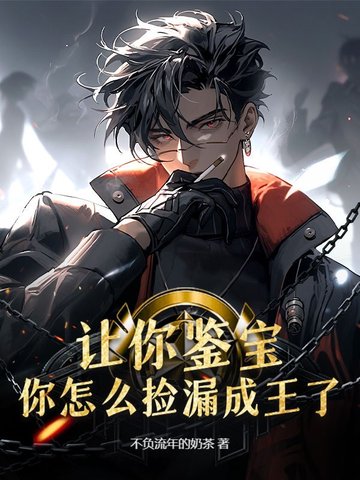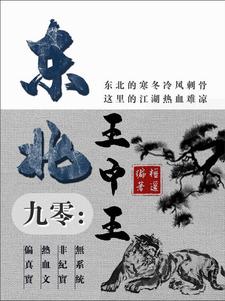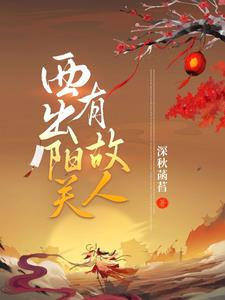第22章 母亲的陶碗经济学
郭静第一次翻开母亲的陶艺笔记,是在十八岁生日那天。梅雨季的潮湿渗进阁楼木板缝,把那本用蓝布包裹的笔记本泡得发胀,纸页边缘蜷曲如老陶碗的豁口。她蹲在落满蛛网的楼梯间,指尖刚触到封皮上“李桂兰”三个字,就有细小的泥粉簌簌掉落——那是母亲年轻时的名字,如今只在市集摊位的吆喝声里,被唤作“老郭家的”。
笔记的第一页用铅笔写着“粗陶碗成本核算”,字迹娟秀得不像终日与泥料打交道的手。郭静凑近窗缝透进的微光,看见母亲用不同颜色的线头标注数据:土黄色棉线勾出“黏土0.5斤/碗”,靛蓝丝线缀着“釉料钱0.12元”,最后用红毛线在页脚打了个死结,写着“售价需≥1.2元”。那是1987年的物价,一碗阳春面才卖两毛五。
“看什么呢?”母亲的声音突然从楼梯口传来,木屐底蹭过青石板的声响让郭静想起窑炉里陶坯开裂前的微颤。她慌忙把笔记本塞进床底旧木箱,却在盖上箱盖前瞥见最后一行字:“若想做星子碗,需偷藏三分金砂——但生计要紧,此页撕毁。”
母亲的陶碗永远有统一的口径和厚度。郭静小时候总蹲在拉坯机旁,看母亲的手掌像圆规般旋转,泥坯在她掌心隆起的老茧下渐渐成形。“碗底要厚三分,盛热汤才不会烫手。”母亲说着,用竹刀在碗底刻下三道浅痕,“这是给张屠户家定做的,他婆娘要坐月子,得用结实碗。”
市集上的陶碗摊位是母亲的战场。她总把郭静打扮成招财童子,坐在堆成小山的粗陶碗后,自己则举着豁口碗演示:“看这胎质,敲起来当当响!”有次隔壁摊位的瓷器贩子笑她碗底厚得能砸核桃,母亲抄起一只碗就往石板上磕,釉面迸裂的纹路竟像极了冬日窗上的冰花。“厚?”她把碎碗片塞到那人手里,“你家婆娘喝鸡汤时,是要碗底先烫穿还是咋地?”
郭静十二岁那年,母亲接了笔急单——给镇上酒厂做两百个酒坛。连续半个月,窑炉昼夜不熄,母亲的手被陶土磨出一层又一层硬茧。某个深夜,郭静被咳嗽声惊醒,看见母亲正借着月光检查酒坛,每只都要倒扣在石板上敲三下,“当当当”的声响里,她听见母亲用方言念叨:“一响二闷三裂纹,这只可惜了。”
那只“可惜了”的酒坛被母亲藏在柴房角落。郭静偷偷去看,发现坛口有道极细的冰裂纹,像新月落在釉面。她用指尖描着纹路,忽然明白母亲为何总在深夜对着窑炉叹气——那些被她亲手判了“死刑”的次品,裂纹里藏着月光的形状。
“学捏碗先学算账。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厨子穿越傻柱之生五娃三子两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公子下班了)的经典小说:《厨子穿越傻柱之生五娃三子两女》...
- 452867字05-05
- 追燕
- 505604字09-10
- 敢爬墙就操死(1v2)
- 566193字12-22
- 让你鉴宝,你怎么捡漏成王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不负流年的奶茶)的经典小说:《让你鉴宝,你怎么捡漏成王了?...
- 408806字07-14
- 九零:东北风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梧遥)的经典小说:《九零:东北风云》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8056880字09-11
- 西出阳关有故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深秋菡萏)的经典小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772204字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