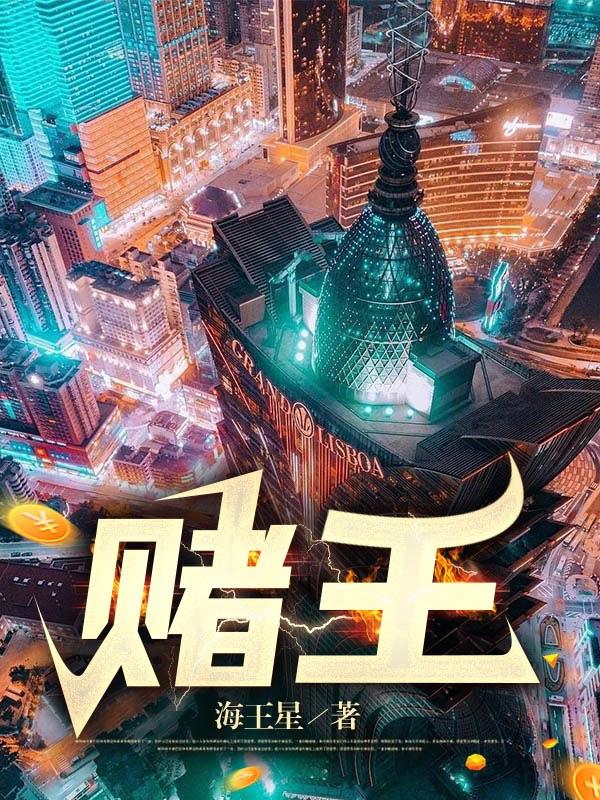第16章 窑变失败的星空瓶
郭静第一次尝试在釉料里撒金粉的那个清晨,景德镇的天空正下着细密的雨。陶溪川老厂房的天窗漏下几束光,照亮她工作台上那只未上釉的陶瓶——瓶身是她熬夜拉坯成型的,弧度模仿着去年在婺源看到的星轨,瓶颈处故意留下几道粗糙的指痕,像星星拖拽的尾迹。
“金粉要趁釉料未干时撒,不然会沉底。”隔壁作坊的老师傅隔着窗喊了句,声音被雨丝浸得发闷。郭静“嗯”了一声,指尖捏着的铜勺却在半空停住——那勺金粉是她用三个月卖茶杯的钱换来的,细如尘埃,在光线下泛着暖昧的红光,像某种凝固的火焰。
她想起七年前那个炸裂的陶碗,火星飞溅时,釉面下隐约有金色的斑点。外婆说那是“窑宝”,是火神赐予的意外之礼。从那时起,郭静就想烧出一件真正能留住星光的作品,让那些转瞬即逝的美,能在陶土中获得永恒的肉身。
釉料是她自己配的:景德镇特有的高岭土,磨成粉后混入蓝铜矿粉末,再滴几滴松节油——老师傅说这样能让蓝色在窑火里“流动得像银河”。她用鬃毛刷蘸着釉料,在陶瓶表面刷出深浅不一的蓝,靠近瓶口的地方浓得像子夜,越往下越淡,直到接近瓶底时,已变成带着银灰的雾蓝,像黎明前的天色。
撒金粉的过程比想象中艰难。郭静屏住呼吸,指尖微颤,铜勺里的金粉簌簌落下,在湿润的釉面上形成不规则的斑点。她本想撒出猎户座的形状,可手一抖,金粉便聚成了一小团,像一滴凝固的血。她慌忙用竹刀去拨,却把釉面划出一道痕迹,露出底下土黄色的陶坯。
“完了。”她心里咯噔一下。但很快又安慰自己:窑变本就是不可预测的,或许这道划痕会成为独特的印记。她小心翼翼地把陶瓶放进窑炉,看着它被层层叠叠的匣钵包围,像一颗被群星簇拥的行星。封窑门时,雨水顺着砖缝渗进来,在她手背上留下一道冰凉的痕迹。
等待的七天像被拉长的陶泥。郭静每天都会去窑炉边,把耳朵贴在砖墙上听里面的动静。老师傅说窑火在夜里会唱歌,只有真正懂陶土的人才能听见。她试着分辨那些细微的声响:松木燃烧的噼啪声,釉料融化的滋滋声,还有陶土在高温下收缩的细微爆裂声——像极了小时候外婆讲故事时,火塘里木柴爆裂的轻响。
开窑那天,阳光异常明媚。郭静蹲在窑炉前,看老师傅用长柄叉取出第一只碗,釉色均匀,是标准的天青色。第二只、第三只……都中规中矩,直到老师傅喊了声“小心”,那只星空瓶才缓缓移出。
郭静的心跳几乎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崩沙卡拉卡)的经典小说:《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最...
- 842906字09-19
- 有半毛钱关系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真的没得事)的经典小说:《有半毛钱关系吗?》最新章节全文...
- 567159字07-24
- 赌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海王星)的经典小说:《赌王》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新...
- 5092744字07-02
- 高中毕业就出道
- 4033418字07-17
- 斩神:炎帝萧炎代理人,开局焚诀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招财小汪汪)的经典小说:《斩神:炎帝萧炎代理人,开局焚诀》...
- 1436611字07-19
- 美男要撩我,我有空间通通收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生花趣味妙笔)的经典小说:《美男要撩我,我有空间通通收下》...
- 885219字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