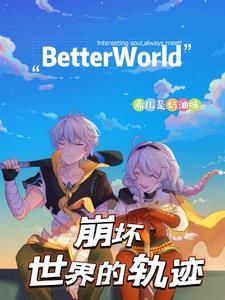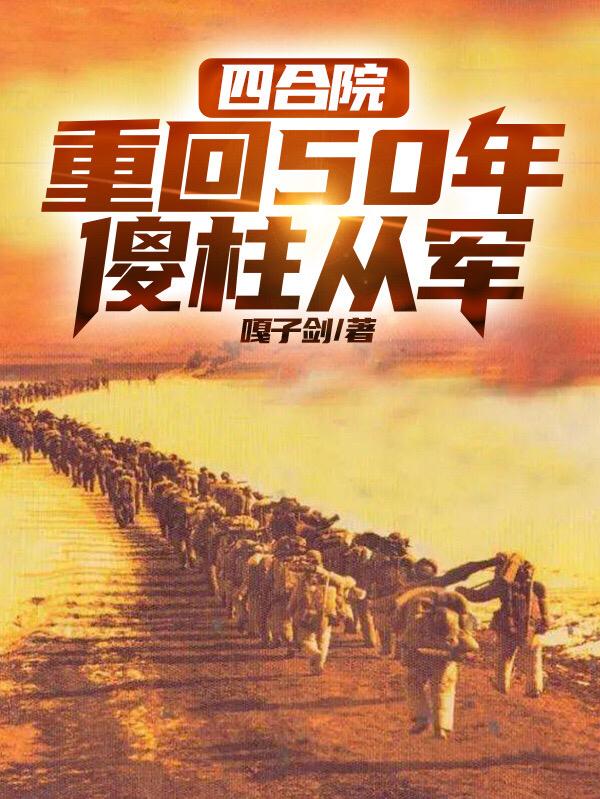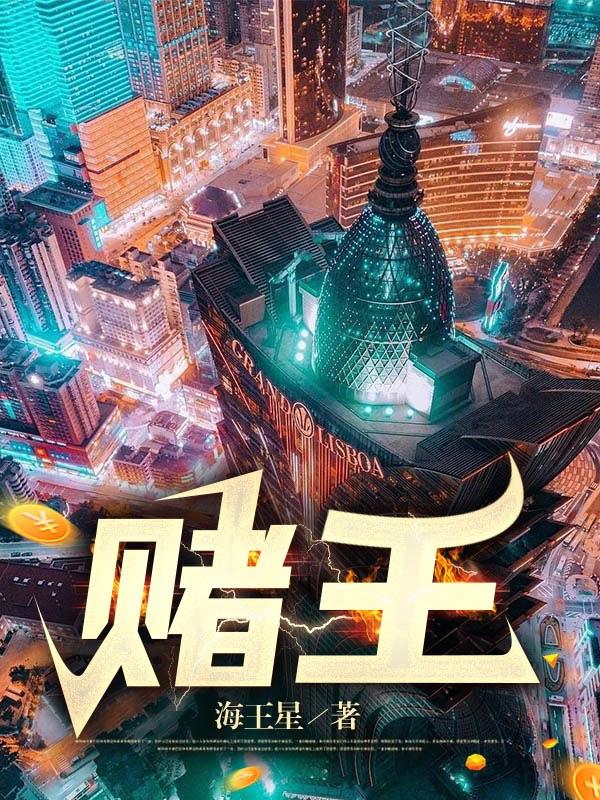第7章 玻璃幕墙与陶土指纹
觉自己在提案书背面画满了指纹——一圈圈螺旋,像某种未被破译的星图。
下午的讨论陷入僵局。甲方要求所有立面采用超白玻璃,理由是“现代感”,而赵环坚持在转角处留出三米见方的实墙,“用来做雨水花园,收集的水可以灌溉屋顶菜园。”话音未落,会议室里响起压抑的笑声。总建筑师拍了拍他的肩膀:“小赵,有想法是好的,但商业不相信诗意。”赵环看见对方袖口的袖扣闪着冷光,像极了玻璃幕墙上的金属连接件。
散会后,他留在会议室收拾资料。夕阳从百叶窗的缝隙斜切进来,在玻璃幕墙上投下条纹状的光影,让那些冰冷的反射面忽然有了温度。他鬼使神差地摸出裤兜里的碎陶片——那是今早路过陶艺作坊时,从废料堆里捡的,表面还留着清晰的指纹凹痕。指尖划过纹路,他忽然想起大学选修课上,那个讲《考工记》的老教授说过:“上古匠人会在陶坯上按指纹,像给器物一个生命的印章。”
提案书的最后一页是经济测算表。赵环的钢笔悬在“外立面材料”一栏,墨水滴在“Low-E玻璃”旁边,晕开一小团蓝黑。他想起父亲常说的“工程思维”:所有变量都要转化为数字,所有情感都要换算成成本。可当他在测绘老城区时,那些被磨圆的门墩石上的指纹凹痕,又该用怎样的公式计算?
凌晨三点,赵环还在修改图纸。建模软件里的玻璃幕墙像一块巨大的冰砖,他试着在转角处“挖”出一个凹槽,系统立刻弹出红色警告:“结构受力不匀”。他关掉警告框,调出卫星地图,找到老城区那棵被他保护下来的香樟树——此刻它的影子应该正投在某个阳台的瓷砖上,像一幅天然的拓印画。
忽然,他想起童年时在祠堂摸到的苔藓。那些微小的植物用湿润的触感告诉他,建筑不该是隔绝人与自然的容器,而应该是两者的接口。他切换到手绘模式,在转角实墙的位置画下一个不规则的曲面,像被手捏过的陶土块,边缘留着深浅不一的指痕。“就叫它‘陶土墙’吧。”他喃喃自语,屏幕光映着他眼底的红血丝。
第二天提案前,赵环把修改后的图纸藏在文件袋最底层。总建筑师提前找他谈话:“甲方点名要全玻璃,你别太固执。”他看着对方身后的城市模型,那些玻璃幕墙的楼宇像一排锋利的牙齿,咬碎了傍晚的云霞。“我只想试试。”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像当年在父亲面前坚持要学建筑时那样。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会议室里,甲方代表果然在看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崩沙卡拉卡)的经典小说:《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最...
- 842906字09-19
- 有半毛钱关系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真的没得事)的经典小说:《有半毛钱关系吗?》最新章节全文...
- 567159字07-24
- 霁月难逢
- 534385字09-09
- 崩坏:我的姐姐是草履虫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希儿是奶油味)的经典小说:《崩坏:我的姐姐是草履虫》最新...
- 1930980字07-26
- 四合院:重回50年,傻柱从军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嘎子剑)的经典小说:《四合院:重回50年,傻柱从军》最新章节...
- 2306992字11-15
- 赌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海王星)的经典小说:《赌王》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新...
- 5092744字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