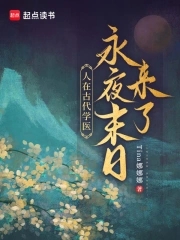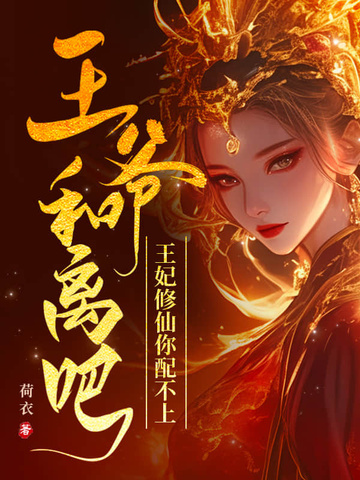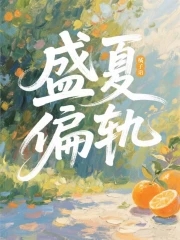第215章 岐仁堂的昼夜钟
生完孩子,脸色苍白得像宣纸,抱着孩子直打哆嗦:“白天怕冷,盖两床被子还觉得风往骨头里钻;夜里又发热,心口烦躁得想掀被子,孩子都抱不住。”
她的脉摸上去浮而无力,像风中的棉线,舌质淡得几乎看不见血色。岐大夫叹了口气:“这是‘重阳无阴’的险证。《灵枢》说‘昼则发热、烦躁,夜则发热、烦躁,是重阳无阴’,您这是生产时失血太多,阴液耗损太过,阳气没了阴液的制约,就像脱缰的野马,白天晚上都在作乱。”
小周急得搓手:“那咋办?我妈让我给她炖人参汤,我又怕补得上火。”
“得先救阴,再补阳。”岐大夫取来阿胶,用黄酒泡着,“阿胶像黏合剂,能把失掉的阴血补起来;龟板像深海的寒玉,能收敛浮越的阳气。这是《伤寒论》里的黄连阿胶汤意思,先把‘无阴’的窟窿填上,再慢慢补阳气,就像先修堤坝再引水,不然水来了也存不住。”
陈阿婆听得直咋舌:“原来生病还分白天黑夜,就像咱巷子里的店铺,有的早开门,有的晚打烊。”
岐大夫指着窗外的日头,正慢慢往西边斜:“人身上的阴阳,就像这巷子里的光影,早上向东,中午在顶,傍晚向西,夜里归寂。《黄帝内经》说‘四时之气使然’,这昼夜的阴阳消长,就是人体的‘小四时’。治病得顺着这‘小四时’来,就像种庄稼得看节气,该浇水时浇水,该施肥时施肥,哪能不管白天黑夜瞎用药?”
说话间,小徒弟端来刚熬好的药,白虎汤的清气、增液汤的润气、黄连阿胶汤的稠气混在一起,竟生出种特别的药香。王老师先端起自己的药碗,咂摸了一口:“苦是苦,可咽下去觉得嗓子眼凉丝丝的,像含了块薄荷糖。”
张婶的药里加了点冰糖,她小口抿着:“这药黏糊糊的,倒像小时候吃的秋梨膏,就是带点药味。”
陈阿婆看着他们喝药,忽然想起什么:“前阵子楼里的赵姑娘,白天怕冷,夜里烦躁,连粥都喝不进去,后来……后来就没了。”她声音发颤,“这也是跟昼夜有关?”
岐大夫的神色沉了沉,望着案头的《黄帝内经》:“《灵枢》说‘昼则恶寒、夜则烦躁,饮食不入,名曰:阴阳交错者死’。这就像白天出月亮、夜里出太阳,阴阳彻底乱了套,就难救了。所以治病得趁早,别等阴阳倒错了才来求医。”
小徒弟默默记下这话,往药柜上的铜炉里添了块沉香。香气袅袅升起,混着窗外的桂花香,把整个岐仁堂裹得暖暖的。王老师喝完药,正低头看自己记偏方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人在古代学医,永夜末日来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Tina娜娜娜)的经典小说:《人在古代学医,永夜末日来了!》最...
- 320003字07-07
- 美漫里的恶魔果实
- 美漫里的恶魔果实章节目录,提供美漫里的恶魔果实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1873100字07-06
- 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箭心)的经典小说:《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最新章节全文...
- 525588字12-21
- 王爷和离吧,王妃修仙你配不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荷衣)的经典小说:《王爷和离吧,王妃修仙你配不上》最新章节...
- 326984字07-07
- 盛夏偏轨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橘子语.)的经典小说:《盛夏偏轨》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284892字07-07
- 火影之最强震遁
- 2741927字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