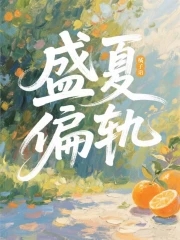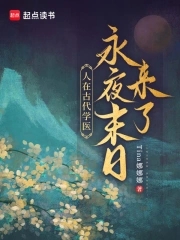第215章 岐仁堂的昼夜钟
像熟透的樱桃。“您这是阳病有余,”他指着窗外的日头,“太阳越盛,您这头疼越凶,就像柴火越旺,锅里的水越沸。《灵枢》说‘昼则增剧,夜则安静,是阳病有余及气病血不病’,您这是气分的热邪在作乱,白天阳气助着热邪,自然疼得厉害。”
王老师摸出个小本子,上面记着自己试的偏方:“我煮过绿豆汤,泡过菊花茶,都不管用。倒是有天夜里失眠,起来看了两页《伤寒论》,竟觉得头不那么疼了。”
岐大夫笑了,提笔写下处方:“您这得用清泻气分热的药。石膏像块冰,能镇住火气;知母像凉扇,能扇散热邪,这两味配着粳米、甘草,就是白虎汤,专治这种白天加重的阳热证。”他顿了顿,又加了3克薄荷,“再加点薄荷,轻浮得很,能顺着经络跑到头上去,就像给闷热的屋子里开扇小窗。”
正说着,巷口卖炒货的老李头扛着麻袋经过,听见动静探进头来:“岐大夫,我那口子更邪门,白天好好的,一到后半夜就发热,翻来覆去睡不着,说是心里像揣着个小火炉。”
老李头的媳妇张婶随后就到,眼圈发黑,手里攥着体温表(她只用来看看,从不说“度数”)。“可不是嘛,”她往门槛上坐,“太阳一落山就开始发懒,到二更天就浑身发烫,想喝凉水,又怕伤着胃,就这么熬着,天亮太阳一出来,热就自己退了。”
岐大夫让她伸舌头,舌质紫暗得像猪肝,舌苔却薄得几乎看不见。按脉时,指下像摸着滑溜溜的泥鳅,沉在底下不肯出来。“这是‘阳气下陷于阴中’,”岐大夫翻开《伤寒论》,指着“热入血室”的条文,“夜里属阴,阳气本该随太阳入里休息,您这阳气却像迷路的孩子,跑到阴分里捣乱,就成了‘热如血室’。”
张婶听得直点头:“可不是迷路嘛!我年轻时在纺织厂倒夜班,天天后半夜干活,是不是那时候把阳气熬乱了?”
“正是这个理。”岐大夫称了15克生地,10克玄参,“生地像深井水,能滋阴凉血;玄参像凉润的玉,能清血里的热。再加点丹皮,能把陷在阴里的阳气引出来,就像给迷路的孩子指条回家的路。这是《温病条辨》里的增液汤底子,专治这种夜热早凉的毛病。”
小徒弟在旁掰着手指头数:“师父,这就有三种病了——夜里重的阴病,白天重的阳病,后半夜热的阳气下陷。那要是白天晚上都难受,该咋办?”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岐大夫还没答话,快递员小周扶着他媳妇进来了。小周媳妇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总裁,你儿子在幼儿园打了你私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夜翡改锥)的经典小说:《总裁,你儿子在幼儿园打了你私生》最...
- 433031字06-28
- 盛夏偏轨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橘子语.)的经典小说:《盛夏偏轨》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284892字07-07
- 人在古代学医,永夜末日来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Tina娜娜娜)的经典小说:《人在古代学医,永夜末日来了!》最...
- 320003字07-07
- 我成帝了金手指才来
- 我成帝了金手指才来章节目录,提供我成帝了金手指才来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14747890字06-28
- 青梅竹马还是他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牵牛花的窗帘)的经典小说:《青梅竹马还是他》最新章节全文...
- 683835字09-11
- 高武:神魔纪元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毁灭尘埃)的经典小说:《高武:神魔纪元》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559910字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