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淮水浊浪与均田暗礁
陈五的官船刚泊在寿春码头,湿热的风就裹着水腥气扑来。他扶着船舷,望着对岸连绵的青瓦祠堂,檐角的铜铃被风撞得叮当响 —— 这声音和甜市的麦浪不同,带着股说不出的闷,像有人拿棉花堵了耳朵。
“大人,” 李昭从舱里钻出来,腰间的横刀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寿春令张元礼在码头上候着,身后跟着二十多个穿绢帛的 —— 瞧那料子,该是本地士族。”
陈五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码头上站着个穿绯色官服的胖子,正用绢帕擦汗,身后的青衫客们交头接耳,有人摇着湘妃竹扇,有人捻着沉香念珠。最前头的白须老者突然提高声音:“陈大人推行均田,北方胡汉欢喜,可咱们淮水两岸,田是祖宗传的,庙是佛祖赐的,哪能说分就分?”
陈五的甜灯在袖底发烫,金砂散成 “礁” 字。他整了整玄色官服,一步步走下跳板。木阶吱呀响,惊得码头上的水鸟扑棱棱飞起。
“张大人,” 他朝张元礼点头,目光扫过人群,“这位老丈是?”
张元礼的胖脸挤出笑:“回大人,这是庐江周氏的周老太爷,淮西首户。”
周老太爷把竹扇往掌心一磕:“陈大人,不是老朽不通情理。我周家的田,是高祖随武帝打天下时赐的;报恩寺的田,是梁武帝御笔圈的‘福田’。您要均田,总得给个说法吧?”
人群里响起附和声。陈五注意到,几个青衫客的袖口都绣着莲花纹 —— 和报恩寺僧人的袈裟滚边一模一样。他摸了摸甜灯,金砂聚成 “寺” 字。
“周老丈,” 他的声音不高,却像块沉石砸进水里,“均田令里写得明白:‘官田、寺田、私田,除祭田、学田外,余者按丁分授。’周家的祭田,陈五亲自画押保留;报恩寺的学田,也留足百亩。至于其余田产……” 他指了指远处的稻田,“您看那田埂,东头是周家的,西头是王家的,中间荒着二十亩 —— 荒的是地,饿的是民。均田不是夺田,是让荒田长稻,饿民有粮。”
周老太爷的脸涨成猪肝色:“好个‘荒田长稻’!我周家的佃户,哪个不是吃我家的粮长大的?”
“周老丈,” 人群里突然挤进来个穿粗布短打的汉子,“我是您家佃户王二牛。您家的田,十亩收八斗租;报恩寺的田,十亩收九斗租。去年涝灾,我家娃饿得啃树皮,您家的粮仓堆得冒尖,寺里的斋饭倒喂了野狗 —— 这田,分得!”
周老太爷的扇子 “啪” 地碎了骨:“反了!反了!” 他身后的青衫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
- 帝御万界
- 一颗神秘的黑珠,揭开了自太古时期的惊天布局,人族大帝,妖族妖皇,灵族灵祖,魔族魔君...
- 150984字10-04
- 让你当伴读书童,你替女少爷考上状元?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二熊出没)的经典小说:《让你当伴读书童,你替女少爷考上状元...
- 345721字07-16
- 修仙別看戏
- 7128898字07-12
- 污染物但是人鱼[第四天灾]
- 1313126字07-13
- 我在修仙界趋吉避凶
- 388001字07-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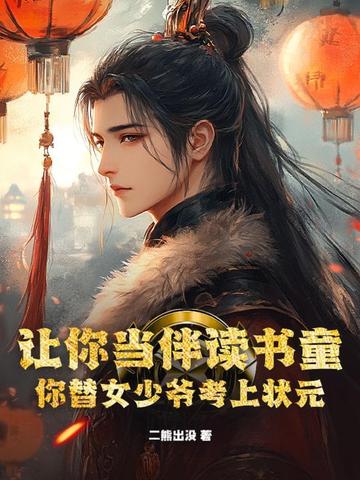

![污染物但是人鱼[第四天灾]](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0/60660/60660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