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无字碑
用"。他想起上个月在军机堂,左相杨国忠拍着他肩膀说:"老将军再立一功,这右仆射的位置就是您的。"可转脸就对张说说:"沈某手握重兵,不得不防。"
三日后,沈铁衣的头颅被悬在朱雀门前。
百姓们不敢信。卖炊饼的王婶端着半盆热粥跪在阶下,粥泼了一地,烫得她直跳脚:"我家狗蛋在渔阳跟着将军学武,说将军教他'枪挑红旗不沾血',这样的人怎会通敌?"卖糖葫芦的老汉把那串插了三年的"沈"字旗扯下来,蘸着粥在地上写:"沈将军是大唐的魂!"
可魂灵终究是被收走了。沈夫人在灵前哭了三天三夜,眼睛肿得像两颗紫葡萄。女儿阿昭才十二岁,蹲在棺材边用草绳编蚂蚱,编着编着就哭出声:"爹爹说要等我及笄那年,带我去看渔阳的雪......"
头七那天夜里,宫里来了个黄门监,捧着块黑檀木匣子。匣子里是道圣旨,还有块未刻字的碑石。"陛下说,"黄门监的声音发颤,"沈将军的功过,留与后人评说。"
沈家村外的山坡上,新坟立起来了。那碑石是从终南山运来的,青黑色,有两人高,碑顶雕着云纹,却没有一个字。村民们蹲在碑前抽旱烟,王婶抹着眼泪说:"这碑空着,倒像将军的心事没说完。"老石匠摸着碑面说:"我在长安见过御碑,刻的都是'功盖三秦'、'德配天地',可这无字碑......"他突然住了嘴,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日子过得慢。阿昭十五岁那年,嫁去了邻村。沈夫人白了头,每天坐在碑前纳鞋底,针脚密得像星星。有人说看见过穿黄衫的公公来上香,可没人敢多问。直到天宝十四年冬天,渔阳的狼烟彻底烧起来了,安禄山的叛军打到了黄河边,郭子仪带着二十万大军去迎敌,路过沈家村时,特意下马拜了三拜。
"沈将军若在,"郭子仪摸着无字碑说,"这叛军哪能过得来潼关?"
宝应元年,新登基的代宗皇帝下旨重审旧案。当年的主审官跪在金銮殿上,浑身发抖地呈上新证据——那几封"通敌"的书信,墨迹是用掺了朱砂的米汤写的,遇水即显,根本不是人血;所谓的军粮亏空,是户部侍郎为了侵吞赈灾粮,故意改了账册。
代宗拍着龙案大哭:"沈卿啊沈卿,朕负你!"他下旨追封沈铁衣为司徒,谥号"忠武",重修沈家祠堂,还派了最巧的石匠去沈家村,在无字碑上刻字。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可石匠到了碑前,却犯了难。原来的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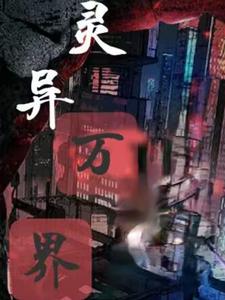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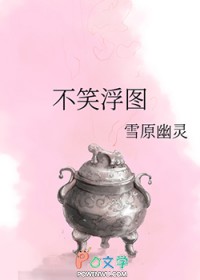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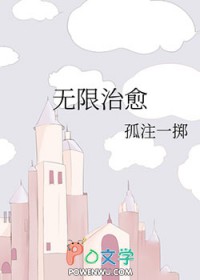


![星际ABO,但玛丽苏[GB]](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61/61892/61892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