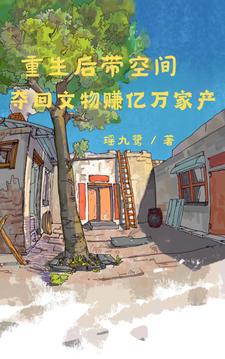第187章 枣园小米粥的「岁月回甘九月十四」
窑洞前的「谷香早餐」:粗瓷与晨露的「岁月对坐」
??八点整,阿妈盛起小米粥——粗瓷碗边缘沾着「米油的黏」,金黄的粥体表面,浮着几颗「煮开花」的小米,热气混着柴火香,在窑洞前的枣树枝间飘散开。李可佳捧着碗蹲在石碾旁——青石板上还凝着晨露,碗底的温度透过掌心,驱散了清晨的凉意,「吹吹再喝,米油烫嘴,却香得扎实。」阿妈递来一碟腌萝卜,「咱陕北人喝小米粥,离不开这口酸,解腻、开胃,跟小米的『甜』配着,才叫日子。」
??用木勺舀起一勺粥,米油挂在勺边「颤巍巍」的,送入口中,先是柴火灶的「焦香」,接着是小米的「绵密」,最后在舌根泛起「清苦后的回甘」——那滋味像极了陕北的黄土塬:表面粗糙,却藏着「阳光晒透的甜」,就像阿妈说的「小米粥要『慢咽细品』,急了尝不出『岁月的香』」。
??骆梓淇拍下她的侧影:粗瓷碗挡住半张脸,碗沿的「米油痕」与身后的「梯田轮廓」重叠,远处的枣园旧址在晨雾中若隐若现,「你发现没?这碗小米粥,跟咱看过的窑洞一样——外表朴素,内里温热,就像当年的延安,用一碗粥,暖了无数人的心。」
四、塬上漫走:从小米到土地的「回甘密码」
??正午的阳光铺满梯田,李可佳跟着阿妈逛「小米田」——塬边的谷穗沉甸甸地弯着腰,金黄的颗粒在风中「沙沙」作响,「咱这小米叫『金裹银』,外壳黄,米芯白,熬粥时『米壳煮化,米芯留劲』,嚼着带点『颗粒感』。」阿妈摘下一根谷穗,指尖搓去外壳,露出饱满的米粒,「去年雨水少,塬上的小米却长得好,黄土地嘛,旱涝都能扛,跟咱陕北人一样,经得起折腾。」
??路过「知青旧居」时,看见窑洞窗台上摆着「旧陶罐」,罐口插着几束干谷穗,墙上的老照片里,知青们蹲在灶台前熬粥,搪瓷碗上的「为人民服务」字样清晰可见。「当年知青娃们刚来,吃不惯小米粥,后来却都说『离了这口粥,心里空落落的』——小米粥啊,是咱陕北的『根』,扎在土地里,也扎在人心里。」阿妈摸着陶罐笑,纹路里藏着「岁月的褶皱」。
??坐在「石碾雕塑」前的石阶上,李可佳忽然懂了:小米粥的「回甘」,原是黄土地的「时光沉淀」——小米用「扎根土地的倔强」,熬出了「耐嚼的甜」;陕北人用「与自然共生的坚韧」,把「粗粮」煮成了「岁月的暖」。就像阿妈说的「黄土地不会亏待人,你种下啥,它就还你啥」,这碗粥里藏着的,分明是「土地与人心」的双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国姓窃明
- 3780952字06-26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573321字06-26
- 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箭心)的经典小说:《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最新章节全文...
- 525588字12-21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空间灵泉带我重生赚亿万家产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瑶九鹭)的经典小说:《空间灵泉带我重生赚亿万家产》最新章...
- 1137083字06-07
- 综漫:从龙珠出包开始修仙之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念起寒舍)的经典小说:《综漫:从龙珠出包开始修仙之旅》最...
- 1967220字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