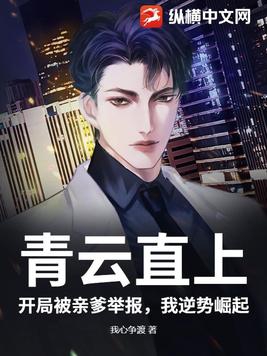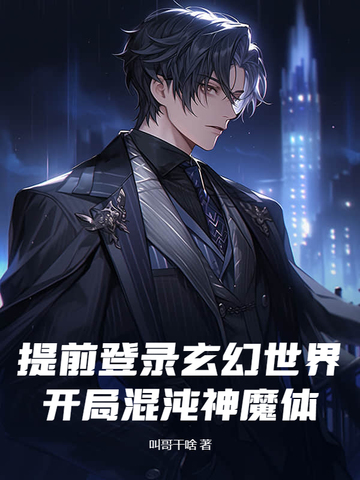第187章 枣园小米粥的「岁月回甘九月十四」
一、晨露里的窑洞村:陶罐与谷香的「时光引子」
??九月十四的清晨,房车停在延安枣园的黄土塬下,车门刚开,一股混着柴火香与小米香的温润气息便漫了进来。李可佳踮脚望向半山——层层叠叠的窑洞嵌在黄土坡上,青瓦窑顶的烟囱飘着细烟,穿粗布衫的阿妈正从窑洞里搬出陶罐,罐口的蓝布巾上,沾着几颗金黄的小米,像给这场「岁月回甘」的味觉之旅,撒了把「时光的谷种」。
??骆梓淇背着相机穿过「知青旧路」,镜头扫过路边的「陕北农耕雕塑」——1930年代的农民弯腰收割小米的剪影、现代农人驾驶收割机的浮雕,与眼前阿妈「舀米过筛」的动作形成「跨时空的呼应」。推开窑洞的木门,泥墙上的「小米丰收图」年画泛着旧色,灶台上的搪瓷缸印着「自力更生」的字样,阿妈笑着招手:「姑娘,咱窑洞里的小米粥,得用塬上种的『米脂小米』,熬出来才挂壁、回甘。」
??路过「陕北小米史碑」时,李可佳忽然想起查过的典故:小米古称「粟」,陕北种植史可追溯至仰韶文化,战国时成「秦地军粮」,1930年代,延安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小米粥成了「红色岁月的味觉记忆」。眼前的陶罐上,刻着「1943」的字样,阿妈说那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小米罐』,装过饥荒年的救命粮,也装过丰收时的喜悦」。
二、灶台前的「柴火熬煮」:陶罐与火苗的「时光协奏」
??七点整,李可佳蹲在柴火灶前,看阿妈淘米——陶罐里的小米倒在粗陶盆中,金黄的颗粒在清水中沉浮,「咱陕北小米要『淘三遍』,头遍去浮尘,二遍留米油,三遍保米香。」手指划过米粒,触感粗粝却温润,「塬上的小米长在黄土地里,喝着西北风、晒着红太阳,颗粒小却油性大,跟咱陕北人似的,看着朴实,心里头有股子『甜劲』。」
??柴火灶「噼啪」燃起,阿妈往铁锅里添了瓢山泉水,「熬粥得用『先武后文』——大火把水烧开,小米下锅『翻个身』,再转小火慢慢『咕嘟』,让米油一点点熬出来。」李可佳盯着跳动的火苗:松木柴烧出的红光映在阿妈脸上,铁锅边缘渐渐浮起「米油层」,像给小米粥镀了层「时光的金膜」。
??骆梓淇的微距镜头对准铁锅:小米粒在沸水中「舒展腰肢」,米油随着热气凝成「细小的泡」,在锅面织成「金黄的网」,「你看这米油,是小米的『魂』,以前陕北婆姨坐月子,就靠这碗粥补身子——黄土地的馈赠,都熬进了这层油里。」
三、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国姓窃明
- 3780952字06-26
- 我的异能盲盒商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离谱了嗷)的经典小说:《我的异能盲盒商店》最新章节全文阅...
- 935031字10-17
- 青云直上:开局被亲爹举报,我逆势崛起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我心争渡)的经典小说:《青云直上:开局被亲爹举报,我逆势崛...
- 302490字03-13
- 提前登录玄幻世界,开局混沌神魔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叫哥干啥)的经典小说:《提前登录玄幻世界,开局混沌神魔体!...
- 349295字07-01
- 玲珑佩之逆世重生:从啃老到传奇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捡拾光阴)的经典小说:《玲珑佩之逆世重生:从啃老到传奇》...
- 972988字06-30
- 我就一实习警察,真没想破案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疯小鸟)的经典小说:《我就一实习警察,真没想破案啊》最新章...
- 1163247字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