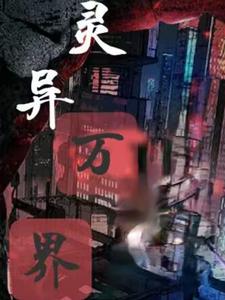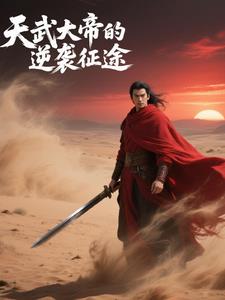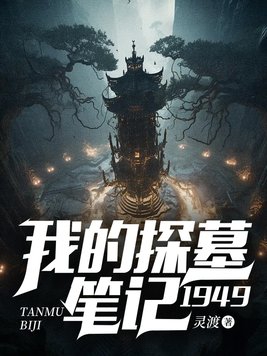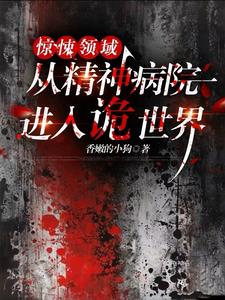第101章 崔判
果野菜,有时是一卷难得的古籍抄本。她仿佛对这世间的寒暑有着天然的淡漠,衣着总是单薄素净,却从未见她瑟缩。更奇的是,她每次出现,都隐隐伴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微凉气息,如同初春融雪时溪涧旁拂过的风,清冽而幽静。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崔子玉心中疑窦丛生,那破庙寒夜里的对话、她提及王魁时眼中闪过的刻骨恨意、以及自己那莫名剧烈的头痛,都如同谜团萦绕不去。然而,柳含烟的谈吐见识却让他深深折服。她于诗词歌赋、经史子集竟有极深的造诣,见解往往精辟独到,发前人所未发;言及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又有着一种超乎年龄的透彻与悲悯。两人常在崔子玉那间四壁萧然、唯有一盏如豆油灯的小屋里,对坐清谈。或论圣贤之道,或品评诗文,或只是静静听着窗外风吹竹叶的沙沙声。每当此时,崔子玉心中便充盈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与熨帖,功名失意的郁结也似乎被这清泉般的话语悄然涤去几分。
这一夜,又是月华如水,透过窗棂,在屋内洒下一片清辉。崔子玉正伏案临摹一幅古帖,柳含烟则安静地坐在一旁,借着月光翻阅他白日里替人写好的书状副本。油灯的光晕在她低垂的侧脸上跳跃,勾勒出柔和的轮廓。
“崔公子这笔字,筋骨内蕴,已有几分卫夫人《笔阵图》的遗意了。” 柳含烟放下状纸,轻声赞道。
崔子玉搁下笔,自嘲一笑:“柳姑娘谬赞。不过是混饭吃的勾当,哪敢攀比古人。倒是姑娘方才所言‘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令子玉感触颇深。只是…” 他话锋一转,目光灼灼地看向柳含烟,带着试探,“只是这世间,恶人逍遥,良善蒙冤之事,比比皆是。便如姑娘曾提过的王县丞,至今仍在任上作威作福,何曾见天理报应?”
柳含烟翻动诉状的手指微微一顿。月光下,她的脸色似乎更白了几分,如同上好的宣纸。她抬起眼,眸中清冷,直视着崔子玉:“公子此言差矣。报应,未必是雷劈电闪,立时三刻。有时,它是一场缓慢的煎熬,如同钝刀割肉,温水煮蛙。” 她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冰冷的穿透力,“王魁此人,贪婪无度,刻薄寡恩,视人命如草芥。他构陷柳家,害人性命,只为掩饰一己私欲。此等恶行,早已刻入骨血,化作他命中的毒蛊。公子且看,他如今虽权势在手,然其心可曾有一日安宁?夜半梦回,可曾不被冤魂泣血之声惊醒?这惶惶不可终日,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便是他日日承受的报应!终有一日,这毒蛊会蚀穿他的心肺,令他众叛亲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7页 / 共20页
相关小说
- 灵异万界
- 灵异万界是由作者6拽著,免费提供灵异万界最新清爽干净的文字章节在线阅读。
- 1401970字04-28
- 天武大帝的逆袭征途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清方观世)的经典小说:《天武大帝的逆袭征途》最新章节全文...
- 607234字05-24
- 精灵:宝可梦模拟人生
- 4134547字07-10
- 我的探墓笔记:1949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灵渡)的经典小说:《我的探墓笔记:1949》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3765996字07-06
- 惊悚领域:从精神病院进入诡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香嫩的小狗)的经典小说:《惊悚领域:从精神病院进入诡世界...
- 1458947字05-12
- 我用娇妻系统称霸星际
- 我用娇妻系统称霸星际章节目录,提供我用娇妻系统称霸星际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1172842字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