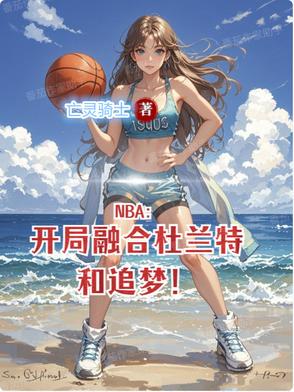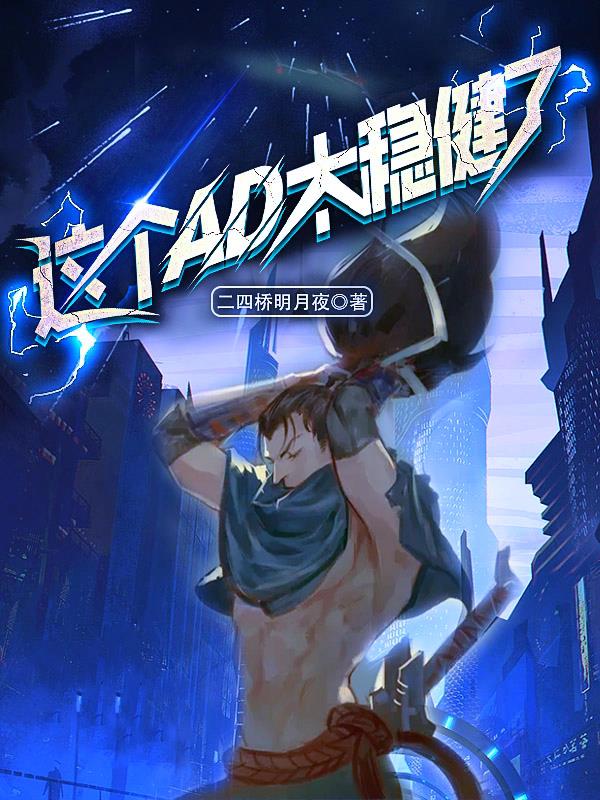第219章
常馒头松软三成,麦香能飘三条街,卖了能换半匹细绢。"馒头的顶部绽开如花,边缘留着蒸笼的竹纹,像极了她常年握面杖的手掌纹路。
酉时的宫宴摆在长乐宫的面坊旁,蒸笼的热气与夕阳的余晖交织,形成一片朦胧的金雾。
陈阿娇亲自给赛义德斟了一杯新麦酒,酒液金黄透亮,浮着一层细密的泡沫。"瞧那边,"她指着面坊深处,"那是文院女徒们在月下用'锦面算盘'计算面粉出口的最优价格,说能算出波斯商人的最高心理价位。"
赛义德捧着酒盏的手微微颤抖,泪水滴在碗沿:"要是早知道汉家女子有这般智慧...我去年就该来长安求师了..."
卫子夫用银匙搅着案上的新麦粥,粥面上浮着一层油亮的麦脂:"我让少府算过,"她轻声道,声音里带着欣慰,"今岁仅面食出口一项赚的钱,就够从西域买三万匹战马,都是女户面坊主们一针一线、一磨一揉赚来的。"
刘妧摸着案头新刻的"市舶令"玉节,玉节上刻着面杖与商船交叉的图案。她想起推行新磨盘时的艰难:先是面匠行会联名抵制,放出"女子掌磨,五谷不生"的谣言,后有老匠在市舶司门前聚众抗议,直到王巧儿的"九穗面坊"用雪白的馒头打开市场,那些抵制的声音才渐渐平息。
面坊的麦香里,混着陈阿娇鬓边的珍珠香与赛义德身上的安息香料味,像一曲跨越国界的技术交流歌谣,在长乐宫的廊下缓缓流淌。
"去叫尚方署的匠人,"刘妧对侍女说,声音里带着笑意,"让他们照着新磨盘的样子,铸一些刻着'工巧利民'的铜范,发到各郡县的面坊去,再铸一批'巧匠之印',给那些有创新的女坊主们。"
"这事哀家早盯着呢!"陈阿娇立刻接话,从袖中摸出一枚铜范样,范面上刻着男女徒共持磨盘的图案,"昨儿工科女徒用面粉袋的韧性计算盔甲内衬厚度,算得比老甲匠还精准,老甲匠现在天天往面坊跑,说是找灵感呢!"
卫子夫则展开一卷空白竹简,提笔蘸墨,笔尖在竹简上顿了顿,仿佛在感受这一笔的重量。"那我便记下,"她的声音清晰而有力,"今日长乐宫议决:设立'器艺局',专司技术交流与改良,凡女户工坊有创新者,赐'巧匠之奖';鼓励技术出口,所得利润按三七分成,工坊得七,朝廷得三。"
竹简便签在暮色中泛着微光,未干的墨字如同一颗投入市舶之海的石子,在大汉的商海之间,漾开层层叠叠的涟漪。刘妧知道,这涟漪终将传遍四海,让更多能工巧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求生:魔法灾变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沐水沧澜)的经典小说:《求生:魔法灾变世界》最新章节全文...
- 1323949字11-23
- NBA:开局融合杜兰特和追梦!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亡灵骑士)的经典小说:《NBA:开局融合杜兰特和追梦!》最新...
- 671439字07-11
- 这个AD太稳健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二四桥明月夜)的经典小说:《这个AD太稳健了》最新章节全文...
- 2312184字07-13
- 乱纪元混沌之局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杂家小生)的经典小说:《乱纪元混沌之局》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665855字07-12
- 大反派也有春天2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熏香如风)的经典小说:《大反派也有春天2》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5461612字07-13
- 穿越00后动漫融合的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喜欢禅菊的刘凯)的经典小说:《穿越00后动漫融合的世界》最...
- 3263140字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