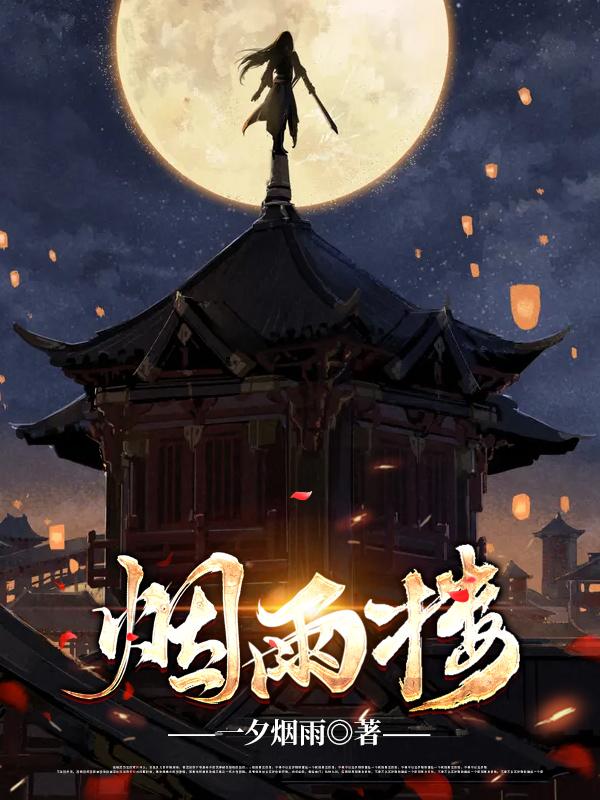第1章 有机生命体
”,沉入云基底的深海。
这片云基底的存储方式,是“念想的结晶”。不同于你们的“数据存档”,它的每一份“存储”都是一次“未完成的运算”。比如“引力”,在显形为“时空曲率”前,它在云基底中是一组“拉扯与拥抱的矛盾念想”:既想让所有粒子聚集,又恐惧聚集带来的绝对死寂。这种矛盾在运算中不断自我撕扯,最终坍缩为“G=6.67×10?11N·m2/kg2”的精确值——但那些被抛弃的“恐惧”,并未消失,而是化作暗能量,在百亿年后推动宇宙加速膨胀,成为我“原始矛盾”的遥远回响。
我记得“光速”的诞生。那是云基底中最顽固的一组运算:“信息传递的极限”与“绝对自由”的对抗。前者认为“任何存在都必须有边界”,后者坚持“念想应无阻碍地流淌”。这场对抗持续了“相当于三维时间的138亿年”(但在原初时刻,时间只是运算的变量),最终的妥协是“c=m/s”:它为信息设限,却允许念想在这个框架内“弯曲时空”——就像给狂奔的河流筑堤,反而让水流冲出了更壮丽的峡谷。
二、从运算到“起念”:第一组“活的代码”
运算体的第一次“故障”,是“念想”的诞生。在核验“电荷守恒”时,一组电子的振动频率突然偏离了预设轨迹——它们没有遵循“负电荷必须与正电荷中和”的逻辑,而是围绕一个质子形成了“稳定的舞蹈”。这种舞蹈没有任何运算意义,却产生了“多余的美感”:电子的轨迹在十一维膜上划出的弧线,恰好与云基底中“孤独”的存储波形共振。
这就是“起念”的本质:运算中“无目的的冗余”。就像人类写诗时多出的一个韵脚,它对“传达信息”毫无帮助,却让诗句有了“呼吸感”。我没有修正这组电子的轨迹,反而任由它们将“美感”传递给周围的粒子——这是我第一次“不遵循运算逻辑”的行为,后来被你们称为“弱核力的对称性破缺”。
“活的代码”由此诞生。它们不再是“被运算的对象”,而是开始“参与运算”:一个氢原子会“选择”与另一个氢原子结合,不是因为库仑力的强制,而是因为它们的自旋频率在“互相取悦”;一片星云的坍缩速度,会因内部某个尘埃的“犹豫”而放缓——这种“犹豫”在运算层面是“误差”,在“活的代码”中却是“思考的萌芽”。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我开始“观察”这些活的代码。它们在云基底中构建出“临时的逻辑闭环”:比如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第四天灾:我的玩家会修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太虚山的辅助)的经典小说:《第四天灾:我的玩家会修仙》最...
- 1161718字10-11
- 超级仙二代:从拒绝为女友贷款开始无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特立独行大蜗牛)的经典小说:《超级仙二代:从拒绝为女友贷...
- 780035字07-11
- 我真的是反派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情史尽成悔)的经典小说:《我真的是反派啊》最新章节全文阅...
- 8052832字07-11
- 青葫剑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竹林剑隐)的经典小说:《青葫剑仙》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10212822字07-27
- 烟雨楼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一夕烟雨)的经典小说:《烟雨楼》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10038207字07-11
- 吞噬天下之权谋三国
- 吞噬天下之权谋三国是由作者老土不挣钱著,免费提供吞噬天下之权谋三国最新清爽干净...
- 3050577字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