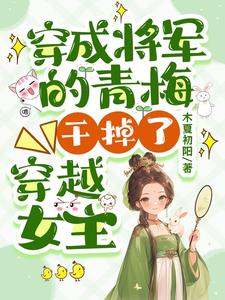第345集:《医师认证体系》
,要标注成“95℃持续12分钟的湿热处理”。技术团队开发的实时翻译系统,后台有17种语言的医学词典,却还是挡不住学员们在讨论区用表情包交流——田中奈奈子画的“阴阳鱼配抹茶碗”,成了课程群的爆款。
约翰的笔记本上,西医的神经分布图旁,歪歪扭扭画着苗医的“筋脉走向”。他总在深夜上线,诊所下班后的凌晨三点,对着虚拟病人练习推拿手法。“在美国,执照就是通行证。”他在小组分享时举起手机,屏幕里是他诊室的照片——原本放止痛药的柜子,现在摆着苗医的药包,“但患者要的不只是合法,是真能解决问题。”
第三章:实操考核的“文化关”
实操考核设在贵阳的苗医实训基地。当金发碧眼的学员们背着竹篓走进苗岭,连寨子里的小孩都追着看稀奇。杨奶奶的孙女阿雅带着他们认药,指着一株开紫花的植物说:“这是‘血见愁’,你们叫它大蓟。但苗医只用根,还要在月圆夜挖才有效。”
奥马尔蹲在田埂上,突然拍手:“我们那里也有这种草!但长老说要和蜂蜜一起嚼,你们是泡酒。”他掏出手机翻出照片,屏幕里的非洲草药和眼前的苗药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叶片边缘更圆些。那天下午,他们在实训基地的黑板上,画满了中非草药的对照图谱。
针灸考核用的是带电子反馈的硅胶人体模型。约翰第一次实操时,手劲太猛,模型立刻报警:“穴位偏移0.3厘米,力度超标50%。”阿雅示范时,银针轻捻慢转,模型的“气血模拟灯”沿着经络次第亮起。“就像给生锈的门轴上油,”她笑着说,“不是蛮力,是找那个‘咯噔’一下的点。”
最让学员们紧张的是“个案诊疗”。每个人要根据虚拟病人的症状,结合当地药材开方。田中奈奈子给“长期伏案的白领”开了“抹茶+杜仲茶方”,还附上茶道式的服药礼仪;奥马尔则把苗医的“退热方”换成了肯尼亚的本土草药,解说时特意强调:“就像我们用不同的鼓点跳同一支舞。”
考核最后一天,杨奶奶突然出现在考场。85岁的老人戴着老花镜,挨个检查学员的药包。在约翰的包里,她发现了一味没见过的药草。“这是我从美国带来的紫锥菊,”约翰紧张地解释,“和苗医的‘清热解毒’药功效相似,能不能替代?”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杨奶奶捻起那株带绒毛的植物,放在鼻尖闻了闻,突然笑了:“苗医的根,是变通。你这孩子,懂了。”
<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穿书成炮灰女配,抢了女主剧本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木夏初阳)的经典小说:《穿书成炮灰女配,抢了女主剧本》最新...
- 1005418字04-19
- 顶级折磨!被傲娇大小姐强掳回家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阿祭)的经典小说:《顶级折磨!被傲娇大小姐强掳回家》最新...
- 1319268字11-15
- 喜欢的人有男友了
- 522097字10-09
- 再走一次修仙路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清静无为)的经典小说:《再走一次修仙路》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508322字04-21
- 总算遇见了总裁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菀儿er)的经典小说:《总算遇见了总裁》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825564字06-16
- 这个顶流他神经病!
- 4735091字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