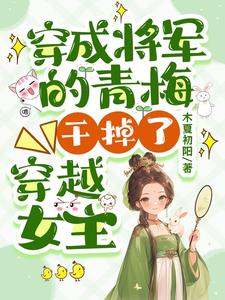第344集:《产业链升级》
《银针刺破长夜时》
一、山雨欲来
暴雨拍打着苗寨吊脚楼的黑瓦,85岁的杨奶奶用布满老茧的手指抚过泛黄的《苗医百草经》。油灯下,那株用朱砂绘制的七叶一枝花正被雨水洇出淡淡的红痕,像极了三年前在非洲义诊时,当地草药师割破手指染红的草药图谱。
“阿宇,机器炒的药,能有火气吗?”杨奶奶的声音混着窗外的雷声,“当年你爷爷炒杜仲,要盯着柴火噼啪响够一百二十声才肯翻面。”
林宇蹲在火塘边,手机屏幕映着他年轻却布满红血丝的脸。屏幕上是德国工程师发来的邮件:“机器人臂关节精度已调试至0.05克,等待古法参数输入。”他指尖划过屏幕上的三维模型——那是座盘踞在黔东南山谷间的银色建筑群,光伏板在效果图里泛着冷光,与身后云雾缭绕的苗岭格格不入。
“奶奶,机器记的不是柴火声,是温度曲线。”林宇从背包里掏出个巴掌大的传感器,“您看,这东西能记下您炒药时的每一秒温度,比人脑准。”
杨奶奶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枯瘦的手紧紧攥住胸口。林宇慌忙去摸药箱,里面却只剩最后一包古法炮制的艾草。这三年,苗药在海外名声鹊起,订单像雪片似的飞来,可寨子里的老药工走的走、老的老,年轻人嫌炮制太苦,宁愿去山外打工。上个月发往迪拜的一批药粉,就因为新学徒没掌握好火候,被退回来时包装上还沾着椰枣的甜腻气息。
“明天奠基仪式,您去吗?”林宇轻声问。
火塘里的柴噼啪爆响,杨奶奶把脸埋进围巾:“我怕机器响起来,山里的药神会跑。”
二、钢铁与银饰
奠基那天,苗寨的芦笙队吹着《踩堂调》,却盖不过挖掘机的轰鸣。林宇站在奠基石旁,看着穿着传统银饰的姑娘们与戴安全帽的工程师擦肩而过,银饰碰撞的脆响和金属器械的钝响奇异地交融。
“林博士,欧盟有机认证的土壤检测报告出来了。”助手小陈递过平板,上面跳动着密密麻麻的数据,“但杨奶奶说的‘阴坡天麻要晒够七七四十九日’,这参数怎么录入系统?”
林宇抬头望向远处的坡地。那里新栽的天麻田埂上,每隔三米就插着根银色传感器,像一排排细瘦的银针刺入大地。他想起上周带德国团队进山采药,老药工阿贵用苗语念叨着“晨露未干不采叶”,德国工程师却蹲在地上,用光谱仪扫描叶片上的露珠。
“把‘四十九日’拆解成湿度、光照、昼夜温差三个维度。”林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穿书成炮灰女配,抢了女主剧本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木夏初阳)的经典小说:《穿书成炮灰女配,抢了女主剧本》最新...
- 1005418字04-19
- 顶级折磨!被傲娇大小姐强掳回家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阿祭)的经典小说:《顶级折磨!被傲娇大小姐强掳回家》最新...
- 1319268字11-15
- 喜欢的人有男友了
- 522097字10-09
- 再走一次修仙路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清静无为)的经典小说:《再走一次修仙路》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508322字04-21
- 总算遇见了总裁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菀儿er)的经典小说:《总算遇见了总裁》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825564字06-16
- 这个顶流他神经病!
- 4735091字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