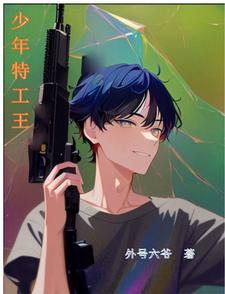第11章 古道热肠
客听见动静,赶紧陪着笑脸把早就备好的租金递过来,有时候还得搭上两句客套话:"您受累跑一趟,这月天儿冷,您多穿点儿。"房东接过钱,也不当面数,往兜里一揣,点点头就算完事。要是碰上手头紧的房客,房东多半也会通融几天,毕竟都是街里街坊的,犯不上为了仨瓜俩枣撕破脸。
这些靠着房租过活的老北京人,日子过得比上班族还舒坦。不用早起挤公交,不用看领导脸色,每天睡到自然醒,沏上一壶高末,端着搪瓷缸子往胡同口一坐,跟老街坊们下下棋、逗逗鸟,一上午就这么消磨过去。下午要是兴致好,还能去澡堂子泡个澡,或者到茶馆听段相声。到了饭点儿,家里要是懒得开火,胡同口的小馆子里要碗炸酱面,切盘酱牛肉,一顿饭也就打发了。反正房租月月都有,只要不胡吃海喝,小日子过得比谁都踏实。
租房的人也是五花八门。有刚进城的打工仔,租间小平房凑合住;有做小买卖的,赁间临街房开个杂货铺;还有跑单帮的生意人,租个院子当仓库。房东对这些房客门儿清,谁老实本分,谁爱惹事,心里都有一本账。碰上靠谱的房客,房租几年不涨都成;可要是遇上邋遢或者闹腾的主儿,到期一准儿撵人,绝不含糊。
当然,"吃瓦片"也不是光等着收钱就完事。房子漏了得修,院墙塌了得补,下水道堵了得通,这些零零碎碎的麻烦事也得房东操心。不过比起上班挣死工资,这点麻烦简直不算什么。更何况,房子越老越值钱,尤其是那些挨着好地段的宅子,放上几年,没准儿就能赶上拆迁,那可是一夜暴富的美事。
我曾经有个老邻居,因为娘家姓那,人称那老太。那老太也是大户出身,当时她都快七十岁了,头发花白,总爱穿一件藏蓝色的确良褂子,胳膊上永远挎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她最值钱的家当——那串磨得发亮的黄铜钥匙。这串钥匙上挂着五把大小不一的钥匙,每把都对应着她那间小院里的出租房。
那老太的小院是祖上传下来的,典型的京城四合院格局,只是早就被隔得面目全非。正房三间改成了两户,东西厢房各住着一家,连倒座房都单独出租了。院当中那棵老枣树还在,树下摆着那老太专属的小马扎,那是她的"办公区"。
记得那时候的每月五号是雷打不动的收租日。这天那老太必定起个大早,先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然后搬着她的小马扎往院门口一坐,帆布包往腿上一搁,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收租有个讲究——从不主动敲门催要,就坐在那儿等着房客主动送上门来。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血色缅北军阀逐鹿为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巨飞雪)的经典小说:《血色缅北军阀逐鹿为王》最新章节全文...
- 1281907字06-30
- 少年特工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外号六爷)的经典小说:《少年特工王》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378397字06-16
- 被拐农女归来,全家日子越过越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云暖暖)的经典小说:《被拐农女归来,全家日子越过越好》最新...
- 587628字10-01
- 超级上门女婿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一起成功)的经典小说:《超级上门女婿》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3737740字06-12
- 被困女子监狱五年,出狱即无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洒家)的经典小说:《被困女子监狱五年,出狱即无敌》最新章节...
- 574659字07-01
- 凝霜之下
- 38768字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