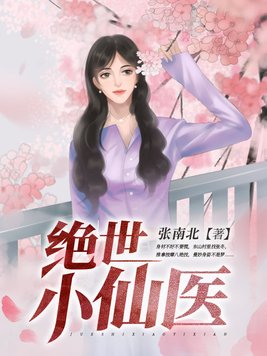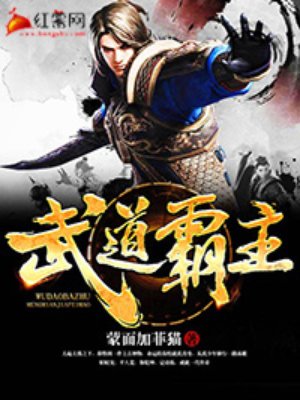第8章 仙人指路1
的关景莲又开口了:“而且啊,现在政策也在鼓励城市更新,大杂院改造是迟早的事儿。到时候,那些平房一拆,原地盖起高楼大厦,你的房子说不定能置换好几套新房呢。”老张还是不太相信,嘟囔着:“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万一不改造呢?”振强拍了拍老张的肩膀,说:“老张,你就别杞人忧天了。我做这方面研究很久了,八九不离十。”我咬了咬牙,心想:反正手里的钱放着也是贬值,不如就听振强的试试。我看着振强,坚定地说:“振强,我信你,我打算试试买大杂院的房子。”振强笑着点点头:“行,我帮你留意着合适的房源。等你买了房,就等着数钱吧。”大家听我这么说,都露出了不同的表情,有羡慕,有怀疑,但我此刻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房产投资上搏一把。
现在想起来,九十年代的京城像一张被雨水洇湿的宣纸,墨痕未干的房改政策在褶皱处悄然晕染。那些揣着大哥大在胡同口转悠的聪明人,总能在蜂窝煤堆里嗅到黄金的气味——当大多数百姓还在计较着单位分房的楼层朝向,他们已经看懂了土地出让合同里藏着的炼金术。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映着他们的倒影,皮包磨出毛边的棱角里,塞满了房管局流出来的内部图纸,纸页边角还沾着计划经济时代最后一滴红墨水。
那时的四合院尚未被称作“文化遗产”,倒像菜市场里被挑剩的萝卜,灰砖缝里嵌着前朝贵胄没带走的落魄气。房管所档案柜里积灰的房契,记录着四十年代某位梨园名旦用八根金条换的跨院,此刻正被某个倒腾钢材的个体户用两万现金打包买断。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站在垂花门下,看测绘队把百年老槐树影投在计算器屏幕上,枝桠间的光斑恰似跳动的数字——东厢房能隔出四间铺面,西耳房拆了改车库,影壁墙推倒后足够停三辆夏利车。他们不懂什么容积率,却知道院墙每向外扩一寸,就能在土地出让金暴涨前多囤一捧金砂。
房改的春风掠过筒子楼时,催生出无数荒诞又精明的生存智慧。某位在机关大院蛰伏半辈子的科员,突然发现自家三代同堂的窘迫,竟成了置换商品房的筹码——他用三环内两间东向阴面房,换得西郊六套毛坯公寓,房本上的面积像发酵的面团般膨胀。而那位总在胡同口修自行车的老汉,某天抖开油腻腻的围裙,露出腰间二十把钥匙叮当作响,每把都挂着不同工地的红绸带。他们交易房产合同像交换香烟般随意,建设银行刚推出的按揭业务,被他们玩成了空手套白狼的连环计。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霁月难逢
- 534385字09-09
- 帝王婿
- 那一夜,他发狂……伤害了她!五年后,他携十万弟子归来……
- 15314934字09-09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绝世小仙医
- 身材不好不要慌,东山村里找张冬,推拿按摩八绝技,曼妙身姿不是梦……
- 13946192字07-01
- 武道霸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蒙面加菲猫)的经典小说:《武道霸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10357703字04-27
- 黑欲人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琅琊刀客)的经典小说:《黑欲人生》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4596424字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