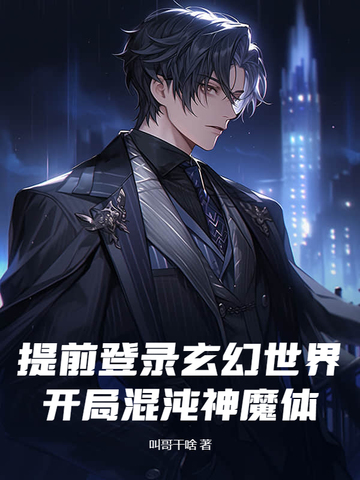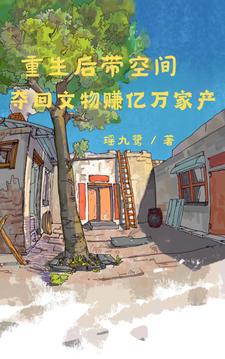第5章 当了教师爷
一个瓷厂当画工,肯定要虚心接受劳动人民的审美需求啊,老百姓审美可不是靠什么抽象想象,主要还是看你画得像不像,最好跟照片一样才好呢。何大师当时的处境,肯定要像匠人画靠拢,但本身呢,他又是张大千的学生,肯定底子是文人画的底子,也就是这样的特定年代,才有这样的东西。放到现在,你让美术学院学生到瓷厂画?可能吗!让何海霞这种大师去,连想也不要想了。这从一定意义上,也算是孤品了。”
老张听我说的是津津有味,也算是有点眼力价,投桃报李地赶紧给我倒了杯茉莉花茶,我呷了口茶,笑道,“您老也喜欢这些东西?”
老张一听我这话,还显得挺激动,赶紧说道,“老弟你是不知道啊,我当兵时候就喜欢读书看报,可我很不走运,在那个时候只能找点《见光大道》《欧阳海之歌》看看,根本看不到古代文化书籍,最多也就是看过批判用的《水浒》,来满足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仰慕之情。后来政策放松了,我看了大量古代小说,不管什么四大名着,还是三言二拍,我都熟读过了;不怕老弟你笑话,我一都看过《金瓶梅》呢!”
1952年的上海,一批蓝布封面的《金瓶梅词话》正在群众手中秘密传阅。泛黄的宣纸页角卷曲如枯叶,每当翻到「潘金莲倒挂葡萄架」这类章节,总有人紧张地瞥向窗外——这是建国初期“新文学规范运动”的狂飙年代,这部明代世情小说被盖上“封建糟粕”的钢印,却在民间化身暗流涌动的“地下文学”。北京琉璃厂的旧书贩子们练就了特殊暗号:轻叩三下柜台问“有兰陵笑笑生的字画吗?”,掌柜便会从佛龛后的夹层掏出用《毛选》封面包裹的私印本,书页间还夹着充当防伪标识的茉莉干花。
转机出现在1957年,一句“《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不可不看!”这句批示让文化部连夜赶制“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奉命开动印刷机,却在删改尺度上犯了难。总编辑王任叔带着老花镜逐字批红,把露骨段落用“□□□”替代,最终诞生的《金瓶梅词话》删去字,硬生生把市井风月改成了“此处省略三万字”的填空题。更绝的是每套书编号发行,需持省军级单位介绍信认购,某位山西老干部误把购书证明写成“研究西门庆同志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为作协流传半世纪的笑谈。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1985年香港太平书局影印的万历本《金瓶梅》裹在尼龙布里偷渡入境,深圳罗湖海关查扣的书籍堆成小山,关员们戏称这是“文字领域的走私黄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国姓窃明
- 3780952字06-26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573321字06-26
- 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箭心)的经典小说:《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最新章节全文...
- 525588字12-21
- 提前登录玄幻世界,开局混沌神魔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叫哥干啥)的经典小说:《提前登录玄幻世界,开局混沌神魔体!...
- 356750字07-01
- 空间灵泉带我重生赚亿万家产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瑶九鹭)的经典小说:《空间灵泉带我重生赚亿万家产》最新章...
- 1137083字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