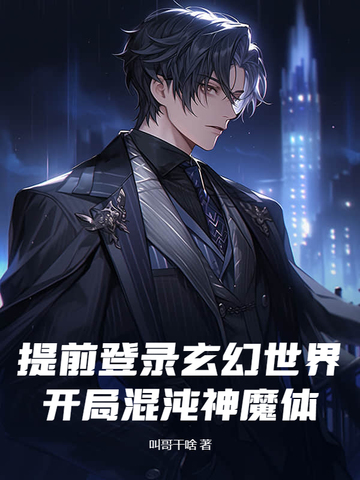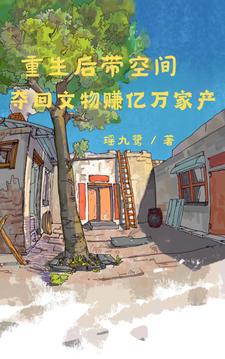第2章 山东大煎饼
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我恨恨地说,“这些人真他妈的给京城人丢脸!”
“老王蹲着收拾碎瓦罐,发现领头的手腕上有块和自己儿子一样的胎记。第二天他多带了份煎饼。人嘛,两个好成一个好,后来这混混成了他干儿子,1994年严打时还救过他一回。”
“哦,这还差不多。”我觉得这总算是给京城人长了脸。其实我也知道,当时很多小混混就是学习古惑仔,本性不坏。
九十年代,《古惑仔》系列电影席卷内地,录像厅里挤满了模仿陈浩南的年轻人。满街都是染黄毛的“山鸡”,校门口突然冒出许多“洪兴帮”,男生们用圆规在课桌上刻“义”字,女生书包里藏着郑伊健的贴纸。台球厅成了“铜锣湾”,五块钱一包的“红梅”烟成了“兄弟”的见面礼,连打架前都要学电影里慢动作甩甩头发。
老派家长痛心疾首,报纸上连篇累牍批判“流氓文化”,可越是禁止,少年们越觉得带劲。直到某天,两个中学生为争“扛把子”名号动了刀子,学校紧急组织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年头,教导主任办公室里没收的砍刀,比没收的课外书还多。
“你是不知道啊,他做的煎饼好吃,人也很灵活,交了不少朋友。后来听他说,常来买煎饼的美院教授,经常用素描换了他煎饼。教授还教他创新,把煎饼做出牡丹花形状,1997年香港回归时在王府井卖"喜庆煎饼",一天净赚八百多。”
听到这,我心里大为震惊,知道做早餐摊子挣钱,没想到这么挣钱。当时普通餐馆,一顿饭也就是花个一二十块钱,一大盘鱼香肉丝才八块钱呢。说起来也许很多人不信,三环附近房价最多1200块钱一平方米……
“就这样,人家就攒了不少钱;九八年京城大规模房改,老王已经在六里桥存了十二万。中介带他看西便门一套42平米的直管公房,产权证上标价九万八。”
反正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这时他摊煎饼也忙,说话也不大动脑子,谁也没有前后眼色,哪里有上帝视角?
过了一会,他说的一个事引起了我的兴趣。
“兄弟,你说摊煎饼什么意思吧,一天到晚成年累月摊来摊去也混不到一间房子在京城,啥世道。俺那个儿子整天笑话俺没见识,不趁着京城房子便宜买一套。”
我感觉他儿子和我一样,都有一股子恨爹不成器的心酸无奈。
“您家公子现在干啥工作啊?”
“学习不好,没上完初中就下学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国姓窃明
- 3780952字06-26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573321字06-26
- 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箭心)的经典小说:《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最新章节全文...
- 525588字12-21
- 提前登录玄幻世界,开局混沌神魔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叫哥干啥)的经典小说:《提前登录玄幻世界,开局混沌神魔体!...
- 349295字07-01
- 空间灵泉带我重生赚亿万家产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瑶九鹭)的经典小说:《空间灵泉带我重生赚亿万家产》最新章...
- 1137083字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