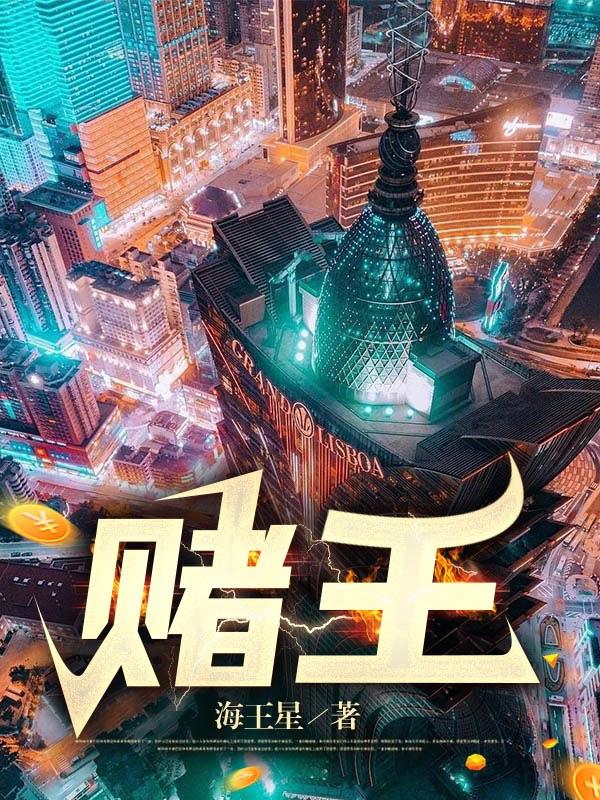第10章 春风十里不如你,爱你妈卖麻花情
《有感三首》)。此“放”字轻巧如释重负,却掩不住残酷逻辑:
买入期:趁贫贱低价购入幼女,“瘦马”之名暗喻其如牲畜般待价而沽。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增值期:投入文学艺术培训,使其身价倍增(《不能忘情吟》载:“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
抛售期:十年间更替三批,色衰则遣散转卖,恰如《旧唐书》所记:“既殁,遣樊素等去”。
---
白居易的矛盾在于其《秦中吟》痛斥“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揭露权贵奢靡;《琵琶行》更借商妇之口泣诉“血色罗裙翻酒污”的玩物命运。
但当涉及自身,却将蓄妓美化为“养才怜艺”。遣散妓女时写《别柳枝》:“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以诗意淡化抛弃实质。更在《追欢偶作》中自诩“当时一部清商乐,亦不长将乐外人”,标榜独占艺妓为清雅之举。
---
唐代严禁官员狎妓,但“家妓”属私有财产,《唐律疏议》视同“婢妾”,可买卖赠人。
白居易曾作《赠内》诗与妻盟誓“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却不妨碍其广纳妾妓。原配逝后更作《自咏老身示诸家属》直言“青衣报平旦,呼我起盥栉”——侍妓晨起服侍,已成老年日常。
其放妓诗常以“马”喻人:“骆马放去蹄间铁”(《不能忘情吟》),看似慈悲解除束缚,实则是榨取价值后的遗弃。
---
白居易诗中的“瘦马”意象,实为后世扬州养妓业的先声:
唐代家妓需精研《霓裳羽衣曲》等宫廷乐舞(见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至明清演变为瘦马必修琴棋书画。
《唐语林》载:“达官家妓坐馆教授,转卖得金无数”,与清代《扬州画舫录》所记瘦马“养女调教,转售盐商”如出一辙。
清人赵翼在《陔馀丛考·养瘦马》中直言:“乐天诗‘莫养瘦马驹’,即今扬州养处女卖人作妾者”,终使“瘦马”污名化定型。
---
“风雅面纱下的千年疮疤”
白居易的“养瘦马”生涯,暴露了士大夫文化的深层悖论:
他们既能以《卖炭翁》刺穿民间疾苦,又能将少女囚作“人形艺术品”赏玩;既可写《妇人苦》哀叹女性命运,又在自家庭院践行人口贸易。这种撕裂,恰是封建特权对人性良知的系统性腐蚀。
当我们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霁月难逢
- 534385字09-09
- 老子修仙回来了
- 林尘,最强仙尊,威名震四方!然而这一天,当他醒来,却是发现自己已经重生少年时。他...
- 11647779字12-25
- 搬空奇葩养母家,下乡替嫁养崽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午后尘埃)的经典小说:《搬空奇葩养母家,下乡替嫁养崽崽》最...
- 1216403字10-07
- 【西方罗曼】高H合集(强制,乙女,美人受)
- 【西方罗曼】高H合集(强制,乙女,美人受)最新章节由网友提供,《【西方罗曼】高H合...
- 336505字04-13
- 赌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海王星)的经典小说:《赌王》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新...
- 5092744字07-02
- 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崩沙卡拉卡)的经典小说:《轰20首飞,你说这是技校搞军训》最...
- 842906字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