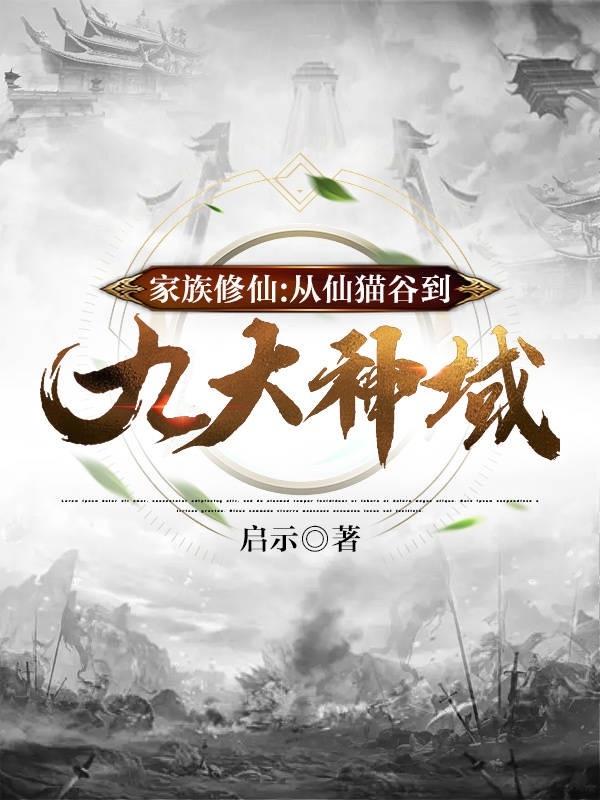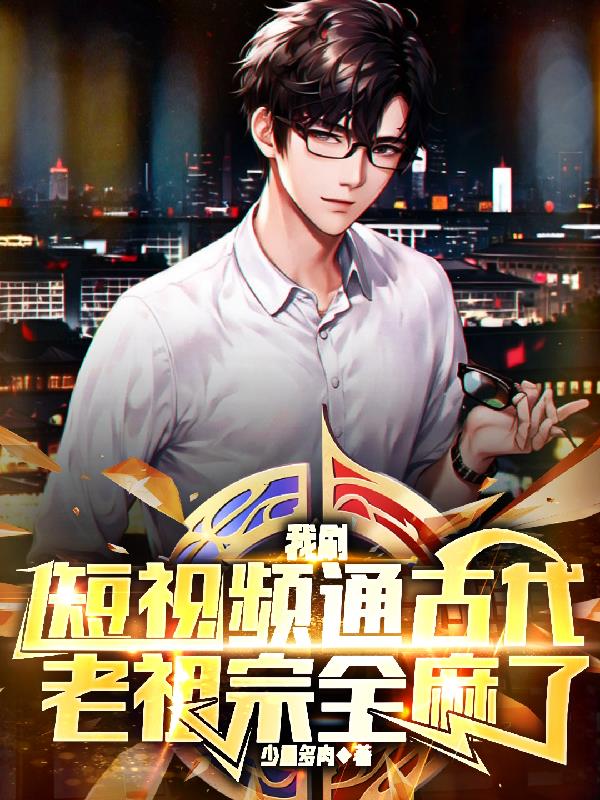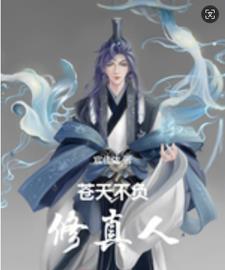第137章 怅然若失
在宇宙尚未被命名的原初时刻,有一种被称为“零分贝之潮”的暗涌,它并非以波长的形式存在,而是以负数的声波在真空里蚀刻出声音的倒影。每一个后来被称为“人”的碳-硅混合体,在胚胎阶段就被这股潮水悄悄打上了出厂编号——不是二维码,也不是DNA,而是一枚无法被任何仪器捕捉的“听觉空洞”。这枚空洞像一枚倒悬的黑胶唱片,凹槽里储藏的不是音乐,而是所有尚未被说出的告别、所有在梦里被撕碎的誓言、所有在母胎里听到的母亲心跳的回声。当人类呱呱坠地,第一口空气涌入肺叶的瞬间,那枚空洞便开始了它的倒计时:它必须在宿主的一生中,不断用外界的声波来喂养自己,否则就会反噬——不是吞噬血肉,而是吞噬“存在感”本身。
于是,在无人、无风、无电器嗡鸣的绝对寂静里,当外界的声波供给突然断裂,这枚空洞便从耳蜗深处开始坍缩。它的坍缩并非三维的,而是在一个被数学家称为“情感第11维”的坐标系里进行:先是所有颜色开始失去饱和度,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拧掉了色相的阀门;接着是温度,皮肤上的每一摄氏度都被换算成一句未发送的微信消息,从指尖蒸发;最后是重力,骨骼与地板之间的万有引力被替换成一种名为“或许”的浮力——你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站在地面上,还是悬浮在一个名为“如果当时”的平行宇宙的罅隙里。
此刻,怅然若失的感觉便如同一群银蓝色的幽灵水母,从你的太阳穴游弋而出。它们的触手不是蛋白质,而是由你此生所有未完成的对话编织而成:小学时没能递出的那封画着海豚的道歉信、青春期在KTV里没勇气点的那首《后来》、面试时卡在喉咙里的那句“我其实会法语”。这些水母在寂静中膨胀,最终形成一个透明的子宫,将你重新包裹成胎儿的姿势。你听见自己的心跳在耳膜内侧敲击出摩尔斯电码,翻译过来是:“此处缺一声叹息,补完可脱离副本。”
但更恐怖的是,这个子宫的羊水是液态的时间。你开始看见十年前的自己正在这个房间里扫地,灰尘其实是记忆的碎屑;又看见十年后的自己站在同样的位置,但地板已经变成了月壤。两个自己同时抬头,隔着二十年的光速向你伸出手,却在指尖相触的瞬间被寂静蒸发——因为寂静不允许“相遇”这种需要声波确认的奢侈行为。你开始理解,怅然若失从来不是“失去”,而是“无法失去”:那些本该被风吹散的往事,在无声中被冻成了琥珀里的蚊虫,永远保持着振翅的姿态,却永远无法完成那个振翅的动作。
在量子层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割鹿记
-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谁人不想去长安。
- 3956967字07-27
- 家族修仙:从仙猫谷到九大神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启示)的经典小说:《家族修仙:从仙猫谷到九大神域》最新章...
- 4321914字07-29
- 洪荒之万界主宰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墨韵2024)的经典小说:《洪荒之万界主宰》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253397字11-21
- 我刷短视频通古代,老祖宗全麻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少面多肉)的经典小说:《我刷短视频通古代,老祖宗全麻了》最...
- 1539306字07-01
- 从一坨答辩开始的克苏鲁神眷之路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深海老母鸡)的经典小说:《从一坨答辩开始的克苏鲁神眷之路...
- 705290字12-19
- 苍天不负修真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宸佳依)的经典小说:《苍天不负修真人》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2310328字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