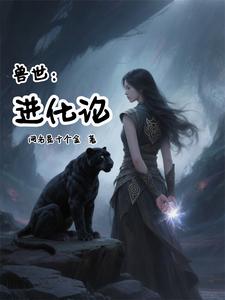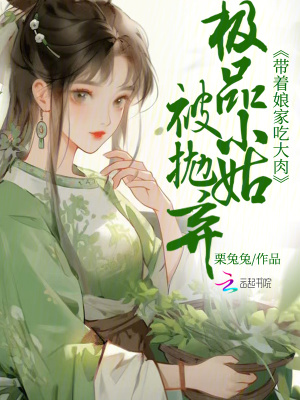文字的风暴才刚刚开
竹笔上的竹叶暗纹里,隐隐流转着神秘符文,仿佛在提醒他:这荒诞的奇遇,或许才刚刚开始。
自那场墨劫风波后,沈砚卿的书摊前再无人敢嗤笑。过往那些冷眼相向的商贾,如今捧着黄金求他挥毫;曾经欺凌过他的地痞,远远望见他的身影便绕道而行。他手中的竹笔成了比刀剑更可怖的利器,街头巷尾传言,但凡惹恼这位书生,笔下墨字便能化作枷锁,将人困在无尽的咒文幻境中。
每日清晨,沈砚卿的摊前总会摆着各地送来的珍奇墨锭与上等宣纸。绸缎庄老板亲自为他量体裁衣,酒楼掌柜端来热腾腾的酒菜,就连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县丞,路过时也会拱手作揖,赔笑问一句:"沈先生今日可愿移步府上,为小儿启蒙?"
他不再为生计发愁,却也未被这突如其来的尊崇冲昏头脑。闲时仍会在摊前抄写正经经文,只是落笔时,笔尖总会不经意间泛起微光。偶尔有孩童好奇围观,他便温声讲解字句,墨香混着朗朗书声,引得路人驻足——人们不再将这些文字当作灵药,而是真正开始敬畏其中蕴含的力量。
某日,当又一位乡绅捧着田契求他题字时,沈砚卿望着对方卑躬屈膝的模样,忽然想起从前被人砸摊的夜晚。他轻抚竹笔,在宣纸上从容写下"守正"二字,墨痕如流水般渗入纸背,泛起点点星辉。这一刻他终于明白,真正改变命运的,从来不是世人的恐惧,而是这支笔里沉淀了七代的力量与本心。
春末的细雨沾湿青石板时,沈砚卿在书摊前瞥见一抹熟悉的藕荷色裙摆。苏玉瑶撑着湘妃竹伞立在街角,发间新簪的珍珠步摇在雨雾里晃出细碎的光,与三年前她甩在他脚下的定亲信物如出一辙——那时她仰着天鹅般的脖颈,说"穷书生也配谈婚论嫁",字字如冰锥扎进他的心。
"沈...沈公子。"她的声音怯生生穿透雨幕,指尖绞着绣帕,"前日见公子为城隍庙题写匾额,那字端的是...力透纸背。"沈砚卿磨墨的手顿了顿,砚台里的墨汁突然翻涌,映出当年她与富家子弟调笑时,将他彻夜誊写的情诗揉成团扔进荷塘的模样。
"苏姑娘过誉。"他头也不抬,狼毫在宣纸上划出凌厉的弧,"不过是混口饭吃的勾当。"雨滴顺着油纸伞骨坠落,溅湿了她精心绣制的鞋面。苏玉瑶张了张嘴,却被突然闯入的小厮打断:"沈先生!李员外家的公子等着您去开蒙呢!"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看着她欲言又止的神情,沈砚卿忽觉索然无味。他收起竹笔,将墨迹未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精灵:可尔妮的直男男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第五十二天)的经典小说:《精灵:可尔妮的直男男友》最新章...
- 1699699字06-27
- 都市逍遥小神医
- 都市逍遥小神医是由作者花小楼著,免费提供都市逍遥小神医最新清爽干净的文字章节在...
- 726505字12-21
- 兽世:进化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网名是十个金)的经典小说:《兽世:进化论》最新章节全文阅...
- 588652字06-30
- 极品小姑被抛弃?带着娘家吃大肉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栗兔兔)的经典小说:《极品小姑被抛弃?带着娘家吃大肉》最...
- 756102字07-01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573321字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