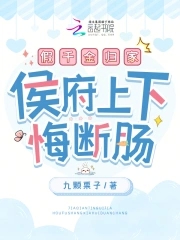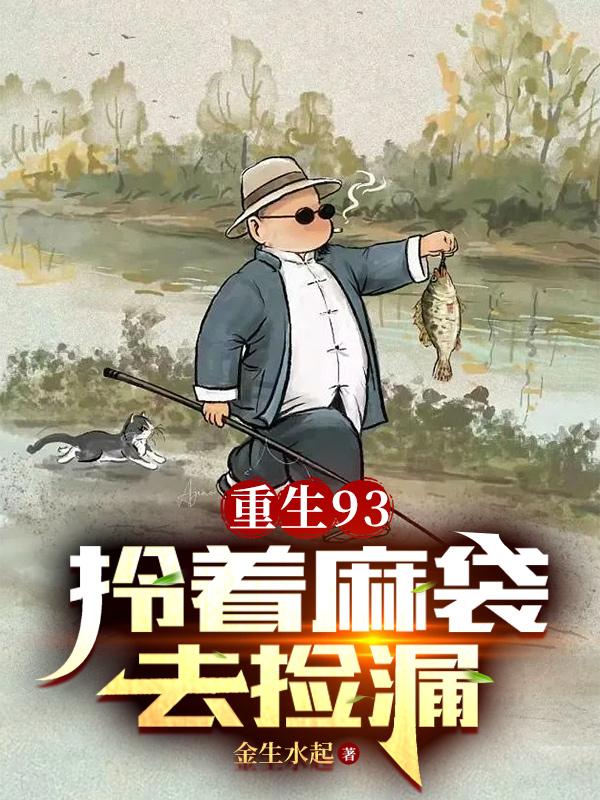第398章 尼木县:经书草原,相互守望
在从仁布县前往尼木的途中,我的车一路伴着雅鲁藏布江而行。初夏的阳光洒落江面,水波闪烁如碎银,那些时而跃动的白帆与低伏的牛羊,使这景致恍若一幅流动的藏地画卷。我的心,安静得像一首沉吟中的古诗。
此行将进入的是尼木县——一个名字在藏语中意为“圣地”的地方。但这里的“圣”,并非源自金碧辉煌的殿宇与佛塔,而是流淌在经书之间,藏在每一块木刻里,铭刻在一代代人温润的守望中。
尼木不像其他高原县城那样分布在辽阔草原上,而是隐匿在群山环绕的拉萨河谷中。小城沿山而建,藏式民居依坡而上,与山色交融如一体,仿佛整个城镇从山体中生长而出。
在拉萨河边,我驻足观看一群孩子放风筝。他们的风筝是用手工布、竹篾、甚至写经纸碎片制成的,随风翻飞。一名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跑到我跟前,把一只风筝塞到我手里:“叔叔,这个送你。”
我接过风筝,发现风筝一角印着藏文六字真言,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信仰并不只存在于庙宇中,而是渗透进每一个呼吸和动作。即便是孩子的游戏,也不曾忘却虔诚。
风从山谷之间吹来,我轻轻一放,那只风筝便高高升起。那一瞬,线从指间划过,我的心像被什么牵起——藏地的人们,不是慢,而是稳。他们将信仰当作骨血,将生活过成吟唱。
次日,我驱车前往雕版印经村——吞巴村。村口传来节奏分明的敲击声,那是刻师在将一笔一划刻进木板。村里家家都有手艺传承的长者。
一位白帽老人正在雕刻,我驻足观望。他的动作极慢,每一刀都如同在对佛倾诉。“这一页经文,要刻四天。”他说,“复杂的,要刻七天。”
“不会觉得辛苦吗?”
他抬头望我,眼神清澈如泉,“我不是在雕字,是在续命。”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经文在木板上生长,它们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是信仰的触角,穿越千年。
老人送我一块刻有“缘起”的木牌:“带着它走,不是为了保佑,而是提醒。”我郑重接过。
随后我走进村外一家藏香工坊。年轻女子正在碾磨松柏皮与雪莲,她的手法温柔细致,像是在与风说话。
“我们做香,不为钱,是为让风也慈悲。”她微笑着递我一根新制藏香。
“燃它时,记得闭眼。”
当晚我坐在拉萨河畔点燃那香。闭上眼,香气升起,记忆忽然浮现——父亲年轻时站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勇者可以不活,但不能没活
- 1609267字07-29
- 普通人的重生日常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叫什么名不吃饭)的经典小说:《普通人的重生日常》最新章节...
- 1809326字07-29
- 都市逍遥小神医
- 都市逍遥小神医是由作者花小楼著,免费提供都市逍遥小神医最新清爽干净的文字章节在...
- 726505字12-21
- 战神王爷夜夜来爬墙,王妃她怒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微茫的砂砾)的经典小说:《战神王爷夜夜来爬墙,王妃她怒了》...
- 1244383字06-14
- 假千金归家,侯府上下悔断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九颗栗子)的经典小说:《假千金归家,侯府上下悔断肠》最新章...
- 332519字07-29
- 重生93:拎着麻袋去捡漏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金生水起)的经典小说:《重生93:拎着麻袋去捡漏》最新章节...
- 8159885字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