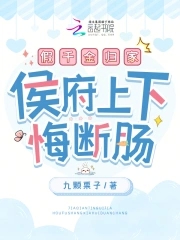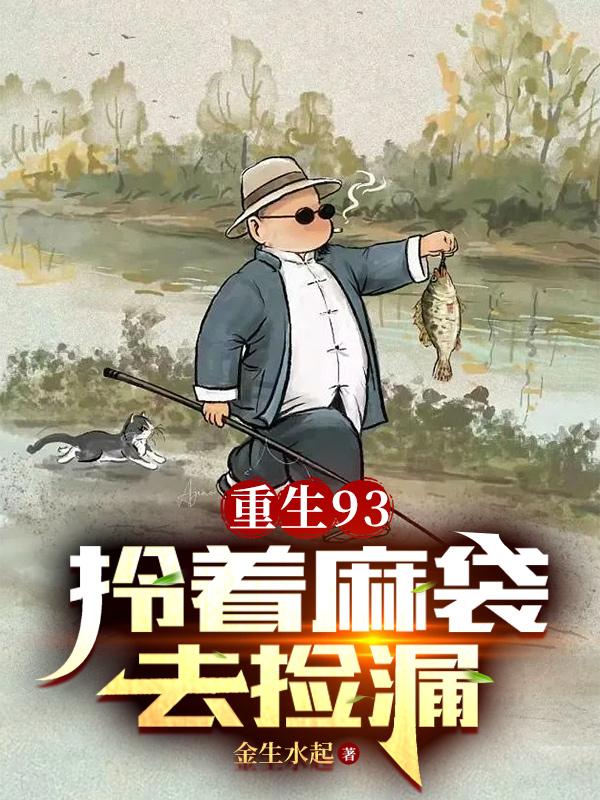第396章 日喀则:双重信仰,雪域都会
离开萨迦那天,一场不大不小的雪落在我的肩头。风将雪化成雾,把山脉模糊在视野之外,我像一个在时空中漂流的旅人,心中却异常清晰地知道:前方,是日喀则。
如果说拉萨是西藏的“心脏”,那日喀则就是它的“脊骨”。这座城市,既承载着后藏的精神命脉,又如一条沿雅鲁藏布江延展的时间之轴,将古与今、信仰与生活、庄严与烟火,一一串联。
当车子驶入市区,天色将暮,我透过车窗看到一座巍峨的建筑在夕阳下披上一层金色。那便是——扎什伦布寺,历代班禅的驻锡之地,亦是我此行最先要探访的所在。
当我踏进寺门,一阵藏香扑面而来。
扎什伦布寺的红墙金顶在夜色中显得庄重而温暖,它不像布达拉宫那般高悬山巅,而是深藏于城市一隅,却自带一种沉静的气场。
寺中僧人告诉我,这里不仅是宗教中心,更是西藏后藏的政治象征。历代班禅都曾在此讲学、主持法事、接见远方而来的使者。
我被引入主殿,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铜质强巴佛像,高达二十余米,气势庄严,细节繁复。灯火下,佛陀的面容仿佛在呼吸,一瞬之间,我竟有些恍惚。
“为何如此巨大?”我问。
一位年长僧人微笑道:“不是佛像巨大,是我们的敬畏太深。”
这句话让我沉默许久。
信仰,有时不需要解答,只需沉浸。
我坐在殿前的石阶上,静静聆听法号与诵经声,那是一种穿透骨髓的震颤感。脑海中浮现一个念头:也许,我们走得越远,越需要停下来,听一听心底最初的声音。
风雪拂面,藏袍轻摆。我看到一个孩子跪拜在佛像前,小小的身影在灯影中坚定如山。我不禁想到:这些静默中的传承,才是高原的真正根基。
那一刻,我的内心竟莫名泛起一种悸动。仿佛这尊佛像不只是供奉的对象,更是某种内在力量的投影。它庞大的不是形体,而是我们面对命运时,心中那份无声的尊崇与宁静。
离开扎什伦布寺,我走进日喀则老城区。这里的街巷弯曲逼仄,商贩叫卖声与远处传来的法号音交织成一种别样的节奏。
我在一家藏餐馆坐下,墙上挂着一幅旧照片——照片中是几十年前的日喀则,路还未铺柏油,山也没有灯光。
餐馆老板是个中年人,他一边炒着酥油包子,一边感慨:“以前我们只有寺庙和牛羊,现在有高铁、机场,还有年轻人回家开咖啡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勇者可以不活,但不能没活
- 1609267字07-29
- 普通人的重生日常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叫什么名不吃饭)的经典小说:《普通人的重生日常》最新章节...
- 1809326字07-29
- 都市逍遥小神医
- 都市逍遥小神医是由作者花小楼著,免费提供都市逍遥小神医最新清爽干净的文字章节在...
- 726505字12-21
- 战神王爷夜夜来爬墙,王妃她怒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微茫的砂砾)的经典小说:《战神王爷夜夜来爬墙,王妃她怒了》...
- 1244383字06-14
- 假千金归家,侯府上下悔断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九颗栗子)的经典小说:《假千金归家,侯府上下悔断肠》最新章...
- 332519字07-29
- 重生93:拎着麻袋去捡漏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金生水起)的经典小说:《重生93:拎着麻袋去捡漏》最新章节...
- 8159885字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