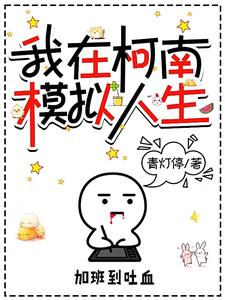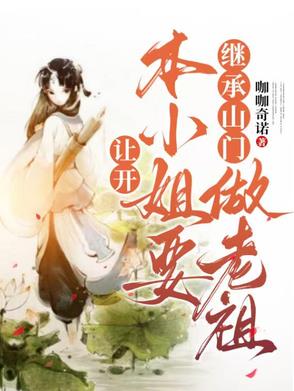第63章 三十秒对话
”
他咬着牙:“有。”
“怎么做?”
“你反问。”
“反问?”
他点头:“你别回答问题,也别提情绪。你只要反问,让对方陷入‘语义回折’状态,系统就会认为你‘信息投递失败’,自动标记为‘低互动反应’,这类数据被认为无效,不会纳入你评分。”
“比如呢?”
“她说她孩子六岁,你说:‘你确定他六岁?不是五岁?’”
我一愣:“这不是扯淡吗?”
“对啊。”老钟咧嘴笑了笑,“可系统不懂扯淡。”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
我犹豫了很久。
这一晚,我在本子上写下几条话术预备稿:
“你为什么这样觉得?”
“你确定你记得?”
“这和你有没有编号有什么关系?”
“你说的是你自己,还是别人?”
我知道我变了。
从一个写实名信、把编号刻进衣领的人,变成了准备用反问句糊弄系统的模糊体。
我心里有种强烈的不适,像在喝自己的冷血。
可我也知道:不这么做,我就会像黄志高一样,被“主动反向折叠”。
**
第五次对话是次日凌晨。
编号者Q-Z888,是个看起来才二十出头的青年,眼神清亮,却略显躁动。
对话一开始,他就怒气冲冲地问我:
“你信这系统吗?”
我本能地反问:
“你问的,是哪一部分?”
他一怔。
“你是问考勤?还是绩效?还是编号管理?”
他迟疑了一下。
我紧跟一句:“你觉得自己是被系统冤枉,还是系统反映了你的真实情况?”
他彻底沉默了。
屏幕判定:“信息未进入有效语义层,访谈中止。”
我得到了系统极高的反馈:
【行为评估:低情绪投入】
【建议延长观测期,待行为趋于稳定后纳入特殊任务延伸组】
我活下来了。
但我从未如此厌恶自己。
**
我站在卫生间镜子前,看着镜中那个说着系统话术、玩着语义游戏、活成冷淡公式的自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573321字06-26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柯南之组织没了我迟早要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青灯停)的经典小说:《柯南之组织没了我迟早要完》最新章节...
- 1104981字05-26
- 时间裂缝:我想回家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红色的稻穗)的经典小说:《时间裂缝:我想回家》最新章节全...
- 747393字07-01
- 她一筐子丹药,改短命大哥绝嗣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咖咖奇诺)的经典小说:《她一筐子丹药,改短命大哥绝嗣命》最...
- 1041602字06-11
- 材料帝国
- 268326字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