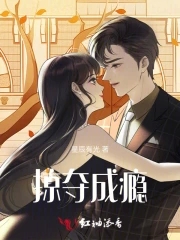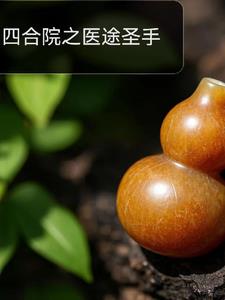第63章 三十秒对话
啪——
窗口黑了。
系统结束了对话。
一条反馈从屏幕上弹出:
【评分上传成功】
【对话方情绪指数:78%|建议警示:适度同理倾向】
【对方认知等级:B级偏移,建议转行为再评估】
【建议话术更新:减少激发性引导】
我盯着那条评语看了好久。
“适度同理倾向。”
系统觉得我“太像人了”。
**
之后三天,我连续被安排了五次“对话任务”。
对象不同,结局相似。
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强装轻松,有的开始痛哭,却被系统“自动切断语义音频”,判定为“扰乱会话”。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像个执行者一样,用最简洁的话提问,再在心里为自己默默扣分。
**
第四天,我遇见了一个女人。
编号Q-K044,年约三十,满脸疲倦。
她开口第一句话不是问我是谁,而是说:
“我孩子六岁了。”
我怔了下。
她继续说:“我当年进厂,是为了孩子上户口。他们说干满三年,就可以申办落户。”
“可现在是第六年了,系统说我的合约在‘黑名片体系’里,没资格。”
“我跟他们吵,他们把我送来了这里。”
她看着我,问:“我是不是疯了?”
我一时说不出话。
屏幕右下角的倒计时只剩五秒。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
“你不是疯了。”
“你是记得自己活着。”
啪——
对话结束。
屏幕这次闪了几次,像在迟疑什么。
然后弹出一行更醒目的提示:
【访谈者风险等级:红黄交叉】
【存在情绪附着激活行为,建议二次评估】
【当前行为可疑:延时表达、共情话术、语调递进】
【系统提示:若继续相似反馈,将被暂列“行为同步风险者”观察组】
我忽然觉得好笑。
我只是说了人话。
可在这套系统里,说“人话”,已经是一种危险行为。
**
我问老钟:“有没有不说话还能过的方式?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箭心)的经典小说:《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最新章节全文...
- 525588字12-21
- 掠夺成瘾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星辰有光)的经典小说:《掠夺成瘾》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470540字07-01
- 都市逍遥小神医
- 都市逍遥小神医是由作者花小楼著,免费提供都市逍遥小神医最新清爽干净的文字章节在...
- 726505字12-21
- 霁月难逢
- 534385字09-09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四合院之医途圣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森林里的啄木鸟)的经典小说:《四合院之医途圣手》最新章节...
- 368322字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