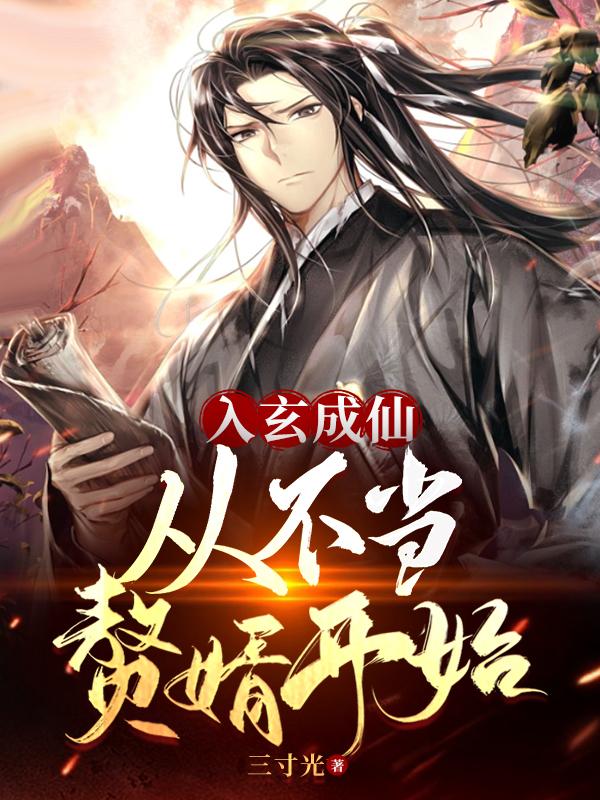第182章 小人物的野望
壶的箭杆弧度都按京城标准削磨。"
话音未落,几个外乡商人挤进来,操着山东口音抱怨:"俺们那儿练的跳远,哪管什么纹路?头回见比赛还得盯着地面使力!"
街角馄饨摊前,老者用旱烟杆敲着板凳:"早年走南闯北,从没见过比赛比得这般精细。
光是标枪握法就分了七八种讲究,能不失分才怪!"他身旁书生摇头叹息。
"这赛事越看越像朝廷练兵——待下届开场,各地健儿怕不是都得照着京城的模子刻出来?"
暮色渐浓时,茶馆伙计举着鸡毛掸子清扫黑板,白粉灰簌簌飘落。新写的赛况里,南方代表队在水上赛艇项目扳回一城,却仍难撼动京城的领先之势。
往来行人驻足时,总有人喃喃:"到底是皇城根儿的气派,连热闹都比别处多几分讲究。"
随着外地客商如潮水般涌入京城,商贸区化作永不熄灭的不夜城。
天未破晓,前门大街的吆喝声已此起彼伏,灯笼次第点亮,子夜时分,商业街的灯火仍与星月争辉,算盘珠子的脆响混着讨价还价声,直闹到更夫打第五遍梆子。
绸缎庄的云锦一匹匹腾空,老字号酱菜缸见了底,就连街边茶汤摊的铜壶都冒了整日热气。
最抢手的当属京城特产,二锅头的酒坛堆成小山,酒气醺得行人迈不开腿;中华自行车的铃铛声穿街过巷,订购单摞起来足有半人高。
自鸣钟、望远镜、老花镜这些手工业品,刚摆上柜台就被抢购一空,掌柜的笑得合不拢嘴,直往伙计手里塞赏钱:"快!连夜补货!"
前门大街转角处的水泥地面被日头晒得发烫,"京华表"的金字招牌下,鎏金铜钟在秋风里泛着晃眼的光。
未到整点,店门口早挤满踮脚张望的人,忽听得齿轮咔嗒轻响,十数座自鸣钟同时撞响《将军令》,激昂乐声惊得檐下麻雀扑棱棱乱飞,连隔壁茶馆的茶客都举着茶碗涌到街心。
四十出头的李东摇着竹扇立在柜台后,棱角分明的脸上带着笑纹。
早年他南下广州,在十三行的西洋钟表铺当学徒,幸得老钟表师倾囊相授,才将西洋钟表的精巧技艺学到骨子里。
前几年回京城创业时,家人变卖田产鼎力支持,又凭借过硬的制表技术,从中华银行拿到一笔低息贷款,这才盘下前门大街的旺铺。
此刻,李东看着伙计们在人潮里打转,眼神里满是欣慰。
穿石青长衫的老学究王鹤龄攥着银票,白须气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炼金术士手册
- 炼金术士手册章节目录,提供炼金术士手册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773159字04-10
- 兽人之附能师
- 96592字05-03
- 大明:如此贪的駙马,朕杀不得?
- 3593287字07-30
- 合格的厨子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用户袁颖人)的经典小说:《合格的厨子》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054288字12-01
- 天统之理想
- 124271字11-07
- 入玄成仙,从不当赘婿开始
- 【轻松+无刀+赘婿(伪)】徐年穿越到玄幻世界,成为大焱望族拒之门外的私生子,在偏...
- 5683270字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