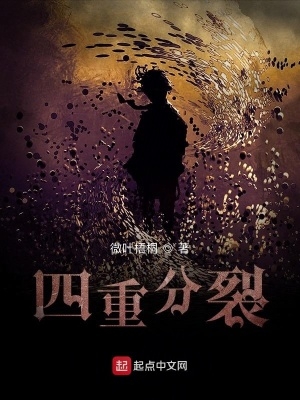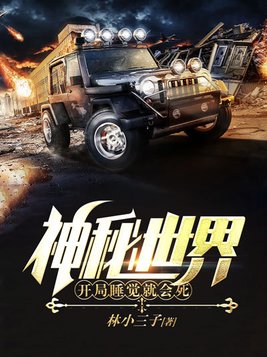第5章 。孤臣陆贽
建中四年的深秋,长安城笼罩在一片肃杀之气中。泾原兵变的叛军已攻入丹凤门,大明宫内乱作一团。二十八岁的翰林学士陆贽抱着一摞奏章,在长廊上疾步而行,青白色的官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陆学士!"一名内侍慌张地拦住他,"陛下已准备移驾奉天,您快些收拾行装吧!"
陆贽眉头紧锁,清瘦的面庞上沁出细汗:"劳烦告知陛下,臣需先将这些奏章整理妥当。"他的声音不大,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远处传来喊杀声,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陆贽却恍若未闻,伏在案前奋笔疾书。当他终于抱着几卷文书赶到宫门时,德宗的车驾已经准备启程。
"陆爱卿,"车帘掀起,露出德宗憔悴的脸,"朕还以为你不来了。"
陆贽深深一揖:"臣岂敢不来?只是这些奏章关乎国事,不敢轻弃。"他递上一卷墨迹未干的纸,"这是臣刚拟的《奉天改元大赦制》,请陛下过目。"
德宗匆匆浏览,眼中渐渐有了神采:"好!好!赦免诸道拖欠赋税,犒赏勤王将士...爱卿深知朕心!"
马蹄声碎,车驾在夜色中向奉天疾驰。陆贽骑在马上回望长安,熊熊烈火中,他仿佛看到了十年前初入长安时的自己——那个十八岁中进士的江南才子,满怀抱负地踏入这座天下中枢。
"陆学士的策论,当为第一。"当年主考官的声音犹在耳边。然而寒门出身的他,即便文采斐然,也只能从华州郑县尉做起。直到三年前,宰相郑馀庆读到他的《均节赋税疏》,惊叹"此王佐才也",才将他推荐入翰林院。
寒风刺骨,陆贽裹紧了单薄的官袍。身旁的同僚瑟瑟发抖:"此番出逃,不知何时能回长安..."
"只要陛下在,大唐就在。"陆贽的声音坚定如铁,"叛军虽盛,终不得人心。"
奉天城中条件艰苦,德宗暂居在一座旧衙门内。陆贽每日伏案至深夜,起草一道道诏书。
他的文笔既有儒者的风骨,又切中时弊,所拟诏令传至各镇,竟使不少观望的节度使纷纷派兵勤王。
这日深夜,德宗突然召见。陆贽踏入临时书房,发现皇帝正对着一封密信发抖。
"爱卿..."德宗将信递给他,"李怀光也反了。"
陆贽心头一震。李怀光是朔方节度使,手中握有精锐边军,他的背叛意味着奉天城危在旦夕。
烛火摇曳,映照着陆贽棱角分明的侧脸。他沉思片刻,突然跪下:"陛下,臣请即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这一世我要享受尽这人间快乐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渭河村夫)的经典小说:《这一世我要享受尽这人间快乐》最新...
- 575298字06-27
- 兽世好孕:娇软兔兔被大佬们狂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豆花芋泥)的经典小说:《兽世好孕:娇软兔兔被大佬们狂宠》...
- 1582627字07-29
- 机甲星辰战记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陈晓堃)的经典小说:《机甲星辰战记》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4198047字07-30
- 四重分裂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微叶梧桐)的经典小说:《四重分裂》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13112831字07-27
- 神秘世界:开局睡觉就会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林小三子)的经典小说:《神秘世界:开局睡觉就会死》最新章...
- 3174520字07-25
- 拥有魔王基因的我,真没想吃软饭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一支威士忌)的经典小说:《拥有魔王基因的我,真没想吃软饭》...
- 3309186字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