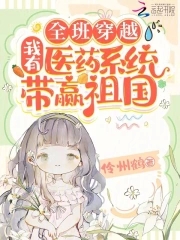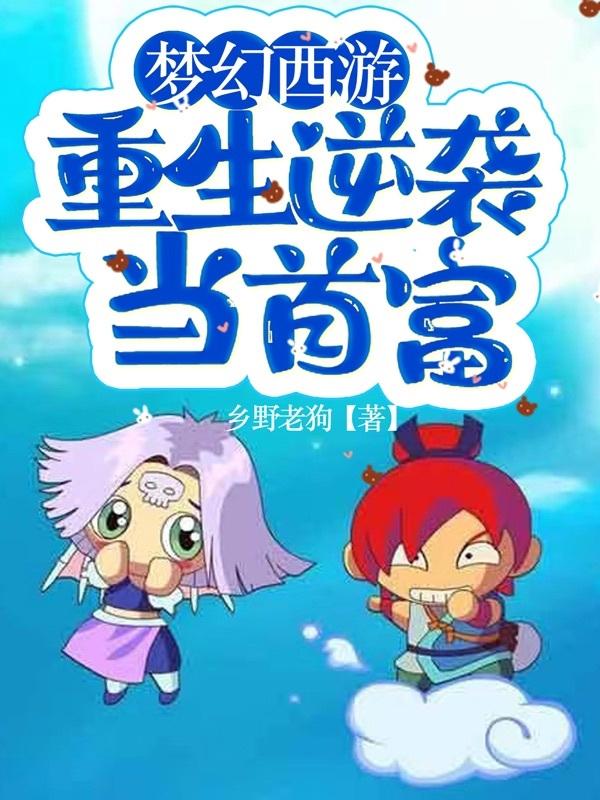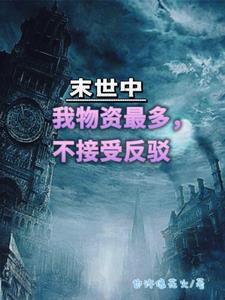《陇原箭芪传》(上卷)
,嘱患者趁热饮下。次日,发热者体温渐降,汗止者气息渐匀,三日后竟能起身劳作。羌人皆叹:“神箭化草,仍护佑吾等!”
第二卷·性味初明,草木相和
黄帝后裔在陇西定居,渐识医药。有巫医名“伯阳”,承先祖观天察地之法,细究黄芪之性。他于不同时节采黄芪:春采苗,味辛轻扬,能散风寒;夏采茎,味甘带温,能助气力;秋采根,味甘醇厚,温而不燥,补力最着;冬采根,则气散味淡,如箭离弦,力已不济。
伯阳悟得:“黄芪得陇原黄土之精,黄土属土,对应人身脾土;其性温属阳,对应人身阳气。甘能补,温能通,故能补脾虚、助阳气。”他见一妇人产后少乳,面色萎黄,食少腹胀,诊其脉弱如丝,曰:“此脾阳不足,气血生化无源。”以黄芪配羊肉炖煮,黄芪补脾气,羊肉益精血,三日后妇人乳水渐丰,面色转红。
又遇一猎户,狩猎时被毒蛇咬伤,伤口红肿,恶寒乏力,脉沉细。众巫医欲投苦寒解毒药,伯阳止之曰:“此毒已伤正气,若徒用苦寒,恐正气崩解。”遂以黄芪为君,配当地所产甘草、防风:黄芪补气以抗毒,甘草解毒以和中,防风祛风以散邪。三药相伍,黄芪得防风则补而不滞,得甘草则温而不燥,恰合“相须”“相使”之妙。猎户服后,次日肿消神振,再服三日,竟能复猎。
伯阳亦发现黄芪之忌:若与萝卜籽同煮,黄芪补气之力大减——盖因萝卜籽性降,黄芪性升,二者“相恶”;若与杏仁同用,杏仁苦降碍气,黄芪温升助气,药力互耗,谓之“相杀”。他将此记于兽皮卷,诫曰:“黄耆补气,忌降泄之物,如箭需顺风,逆则难发。”
陇西农书《陇亩记》初载黄芪种植:“宜选阳坡黄土,忌湿地。春三月下种,需与豆科植物轮作——豆生根瘤,能助土气,土肥则黄芪根壮,如箭杆得沃土滋养,方有穿石之力。”此虽为农法,却暗合“土生万物”“相生相养”之理。
第三卷·六气应病,岁运调方
帝尧时代,陇西遭“太阴湿土司天”之岁,全年湿气弥漫,民多倦怠乏力,肢体沉重,腹泻便溏。巫医们依伯阳旧法,单用黄芪煮汤,却见部分患者饮后腹胀加重。时有游方医者名“巫咸”,遍历各地,见此情形曰:“湿盛则需化湿,单用黄芪补气,恐助湿为患,如箭杆沾泥,难以前行。”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巫咸遂改方:黄芪配苍术、茯苓。苍术燥湿健脾,茯苓渗湿利水,黄芪补气助运,三药共奏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求生:魔法灾变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沐水沧澜)的经典小说:《求生:魔法灾变世界》最新章节全文...
- 1323949字11-23
- 末世:我穿梭两界成霸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小孩骑单车)的经典小说:《末世:我穿梭两界成霸主》最新章...
- 1068137字12-19
- 全班穿越,我有医药系统带赢祖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伶州鹤)的经典小说:《全班穿越,我有医药系统带赢祖国》最新...
- 342058字10-21
- 梦幻西游:重生逆袭当首富
- 梦幻西游:重生逆袭当首富是由作者乡野老狗著,免费提供梦幻西游:重生逆袭当首富最...
- 9499617字07-15
- 灵气入侵:这该死的末世我来终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苏四五)的经典小说:《灵气入侵:这该死的末世我来终结》最...
- 611523字12-19
- 末世中我物资最多,不接受反驳
- 末世中我物资最多,不接受反驳是由作者也许像花火著,免费提供末世中我物资最多,不接...
- 755628字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