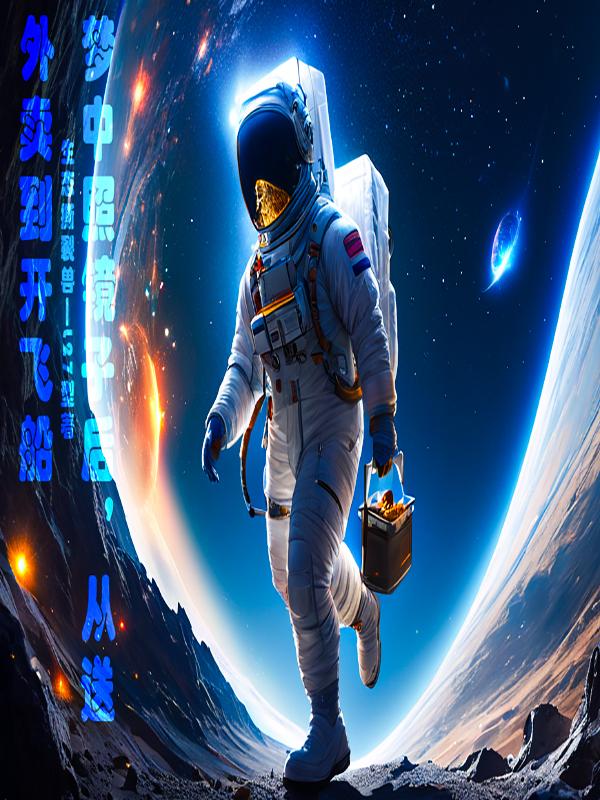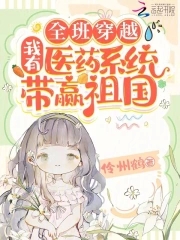《青风峪黄气根》(下卷)
拖着病体,陆陆续续来到陈婆婆家,看着陶罐里翻滚的黄根草,眼里又燃起了希望。老白郎中也来了,他拿起一块根茎,放在鼻尖闻了闻,又掰断看断面的纹路,"色黄入脾,味甘补土,性温能通......老栓爷没说错,这是能'抓'住气的药!"
他让黄芪按"一人一两根,水煎温服"的法子给大家分药。可问题来了:村里有三十多口人,带回的黄根草只够十来个人用。"先给病重的。"黄芪咬咬牙,把药草分成了几份,优先送到了老栓爷、王婶家等最危急的病人炕头。
下卷二:配伍显效,阴阳调和
头三天,药效像初春的嫩芽,慢慢冒了头。
老栓爷能靠着炕沿坐起来了,虽然说话还喘,但能认出人了;王婶家的小女儿能喝下半碗小米粥,小手能抓住娘的衣角;李大爷不再咳嗽,能拄着木棍在院子里走两圈。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些病人喝了药,觉得胸口发闷,像堵着团棉花;还有的人喝了后上火,嘴角起了燎泡。
"这药性太燥了。"老白郎中蹲在老槐树下,拿着根黄根草琢磨,"它补的是'元气',可病人身体里还有湿邪,就像湿柴上浇热油,烧不起来,还冒黑烟。"
陈婆婆这时已经能下地了,她坐在门槛上,捻着从溪边采来的茯苓和泽泻,"黄根草是'阳',得配点'阴'的药。茯苓能祛湿,泽泻能利水,把湿邪排出去,它的力气才能使上。"
黄芪茅塞顿开。他按陈婆婆说的,带着几个稍微好转的村民,去谷底的青石滩挖茯苓,又去西山背阴坡采泽泻。回来后,老白郎中配伍成方:黄根草为主,加茯苓、泽泻各少许,再放两颗大枣调和药性。
这剂药熬出来,汤色黄亮,药香里带着点枣甜。喝了两天,那些胸口发闷的病人,呼吸顺畅了;嘴角起燎泡的,火气也消了。李大爷摸着肚子说:"这药喝下去,像有条暖水流进骨子里,力气慢慢就回来了,不燥,舒服。"
黄芪看着村民们一天天好起来,心里却犯了愁:带来的黄根草快用完了,村里还有一半人没喝上药。"得再去挖!"他扛起药篓就要出门,却被陈婆婆拉住了。
"这草有灵性,"老人摸着他的胳膊,"你上次挖得急,伤了根须。要让它再长,得留种,还得教大家怎么种。"她让黄芪把剩下的黄根草选出最饱满的根茎,切成带芽的小段,又让人在东山脚下开垦出一片向阳的坡地,"这草喜阳,爱喝山泉水,土要松,不能涝——就像咱青风峪的人,得晒着太阳,踩着实土,才能长力气。"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求生:魔法灾变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沐水沧澜)的经典小说:《求生:魔法灾变世界》最新章节全文...
- 1323949字11-23
- 它贴着一张便利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红枫霜月)的经典小说:《它贴着一张便利贴》最新章节全文阅...
- 2635094字07-28
- 泅水(人鬼骨科)
- 泅水(人鬼骨科)章节目录,提供泅水(人鬼骨科)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127326字06-23
- 梦中照镜子后,从送外卖到开飞船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生态撕裂兽l-27型)的经典小说:《梦中照镜子后,从送外卖到开...
- 1635001字10-28
- 全班穿越,我有医药系统带赢祖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伶州鹤)的经典小说:《全班穿越,我有医药系统带赢祖国》最新...
- 342058字10-21
- 母龙是我的作弊手段,我无敌
- 母龙是我的作弊手段,我无敌是由作者户口霸王龙著,免费提供母龙是我的作弊手段,我无...
- 1288311字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