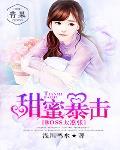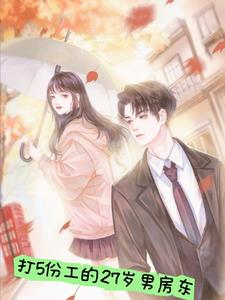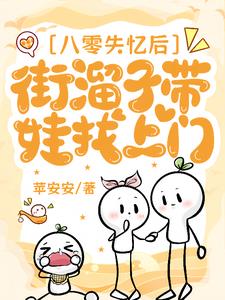第450章 韩来共辅政
因牵涉废后之争被贬,一个称病辞官,如今换上韩瑗和来济,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陛下在朝堂上布的新局。
退朝后,韩瑗回到门下省官署。
属吏们早已在廊下等候,见他过来,齐齐躬身行礼。
他的新官印就摆在案上,铜质的印身刻着 “侍中” 二字,边角还带着新铸的毛刺。
韩瑗拿起印,在废纸上盖了个印蜕,朱红色的印记边缘齐整,他忽然想起永徽元年自己刚任黄门侍郎时,也是这样在案前试印,只是那时的印文是 “黄门侍郎之印”。
“把去年的赈灾奏疏都找出来。”
韩瑗放下官印,指尖在案上的公文堆里翻了翻:
“陇右道的粮价波动得厉害,得重新核一遍。”
属吏应声而去时,他望着窗外的槐树,枝桠上刚冒出的新芽被风一吹,轻轻晃了晃,像极了当年在弘文馆与来济一起抄书时,窗外那棵老槐树的模样。
来济到中书省上任时,史官正在编纂《贞观实录》。
他路过史馆门口,瞥见案上摊着的草稿,上面记着贞观十七年自己任太子冼马时,劝谏李承乾勿要亲近伶人的旧事。
“大人,这是新拟的册封新罗国王的诏草。”
中书舍人捧着卷轴进来,墨迹还带着湿润的光泽。
来济接过诏草,提笔在 “永固藩邦” 四个字旁圈了圈:
“把‘固’字改作‘睦’。” 他想起去年出使高句丽时,见辽水两岸的百姓因战事流离失所,笔尖在纸上顿了顿:
“邦交之道,不在强压,在和睦。”
舍人应着去改,他望着窗外,太极宫的角楼在晨光里露出青灰色的轮廓,檐角的铁马被风吹得叮当作响。
两人的任命在长安官场传开时,西市的酒肆里正聚着些卸任的老臣。
有个曾在贞观年间任过中书舍人的老者,啜着酒叹道:
“韩瑗在绵州做刺史时,单骑入山劝降了作乱的獠人;来济当年随太宗征高丽,在驻跸山亲手斩了敌酋,这两个人,都是有真本事的。”
旁边有人接话:
“可他们都是反对废后的,陛下如今重用,倒是耐人寻味。”
韩瑗的夫人夜里给他整理书箧,翻出他任吏部侍郎时写的《选官策》,纸页都泛黄了,上面用朱笔标着 “取士在德,不在门第”。
“夫君如今入了门下省,更要当心些。”
夫人把策论放回箧中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627559字07-06
- 甜蜜暴击:BOSS太嚣张
- 甜蜜暴击:BOSS太嚣张章节目录,提供甜蜜暴击:BOSS太嚣张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1426885字07-16
- 打5份工的27岁男房东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紫苏土豆)的经典小说:《打5份工的27岁男房东》最新章节全文...
- 1434148字07-03
- 御兽:宠兽养家我有钱花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周周然)的经典小说:《御兽:宠兽养家我有钱花》最新章节全...
- 1153027字07-18
- 我怎么不知道我和街头混混有崽啦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苹安安)的经典小说:《我怎么不知道我和街头混混有崽啦》最...
- 491886字07-16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