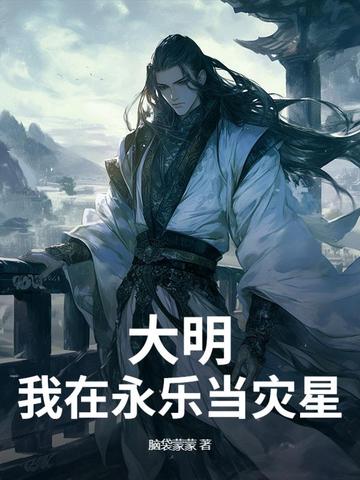第183章 晋怀帝司马炽:在废墟上拼凑帝国的最后努力
永兴元年(304 年)的长安,西北风卷着黄土拍打着秦王府的朱漆大门。二十四岁的司马炽正趴在案桌上,食指跟着竹简上的《左传》逐字挪动,烛火在他清瘦的脸上投下晃动的阴影。自赵王伦篡位以来,他已在书斋里躲了三年,每日与史籍为伴,连窗台上的博山炉都积了薄灰 —— 他太清楚,在这个诸王混战的年代,抛头露面只会招来杀身之祸。
“殿下,河间王的使者到了!” 侍从的通报惊飞了梁上的燕子。司马炽手一抖,竹简上的 “重耳流亡” 四字被墨汁洇开,他盯着晕染的字迹发怔,直到使者捧着策书闯入堂中。
“皇太弟之位,非殿下莫属。” 使者的话像重锤砸在青砖上。司马炽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袖,想起去年惠帝在荡阴被掳,自己在邺城看见的场景:皇帝车驾只剩空辇,六玺不知所踪,随行官员被匈奴骑兵追得跳河,河水都被染成血色。“我一个闲散王爷,如何担得起社稷重任?” 他的声音里带着连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
典书令修肃突然跪下,额头磕在砖地上:“殿下可还记得,去年氐羌骑兵已到泾川?他们在平原郡杀了三万百姓,把婴儿挑在长矛上作乐!” 修肃抬头时,司马炽看见他眼角的泪痕,“如今清河王年幼,唯有殿下的皇族血脉能凝聚人心。当年汉文帝入长安,靠的不也是宋昌等大臣力挺?臣愿做殿下的宋昌!”
案头的漏壶滴答作响,司马炽望着窗外凋零的梧桐 —— 那是武帝亲手栽种的,如今枝干歪斜,像极了摇摇欲坠的晋室。他忽然想起十岁那年,祖父司马昭抱着他坐在太极殿,指着殿上的蟠龙柱说:“炽儿,这是大禹治水的龙纹,我司马家承的是大禹之德。” 如今蟠龙柱还在,大禹之德却早已被诸王的鲜血冲淡。
“也罢。” 司马炽突然站起身,袖中竹简滑落,“就像重耳流亡十九年,终究要面对晋国的烂摊子。” 他不知道,自己这一站,便踏上了比重耳更艰难的流亡路。
永嘉元年(307 年)正月初一,洛阳太极殿。司马炽望着殿下参差不齐的朝臣,发现半数人穿着打补丁的朝服,袖口还沾着去年战乱的血迹。他深吸一口气,展开手中的桑木诏书:“朕愿与诸公修复武帝旧制,每月初一、十五,朕在东堂听政,无论大小政务,皆可直陈。”
黄门侍郎傅宣盯着皇帝清瘦的身影,突然想起二十年前武帝临朝的场景 —— 那时殿中锦帛覆地,如今却连地砖都缺了角。当尚书郎读完月令,司马炽开口问:“荆州刺史山简奏报,流民已达十万,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大明:我在永乐当灾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脑袋蒙蒙)的经典小说:《大明:我在永乐当灾星》最新章节全...
- 517733字05-13
- 长生志怪:从狐妖拜师开始修仙
- 1341670字05-16
- 提前通关,然后进入惊悚游戏
- 2309480字04-13
- 人在皇宫:从升级化骨绵掌开始
- 4768339字05-18
- 人鱼末世求生攻略
- 1115174字04-13
- 万化至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南岳大王)的经典小说:《万化至尊》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750343字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