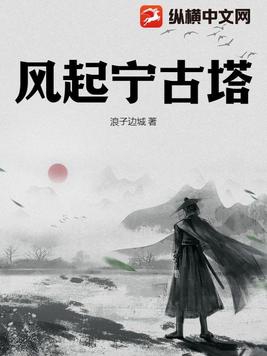第一百八十七章 你是谁?
秋分时,酒楼住进个白发老妪,随身携带的藤箱里装着本泛黄的医书。她每日清晨都要坐在方荡常坐的位置,点一壶菊花茶,翻到某一页便对着窗外发呆。有天方荡路过,见那书页上印着“赵长乐“三个字,正是长乐晚年刊行的那本《民间急救方》。
“老夫人也懂医术?“他停下脚步。
老妪抬头时,眼里闪过丝光亮:“这是先师的书。她说医者仁心,最该治的是'相见难'的病。“她指着书页空白处的批注,“你看这句'千里之外,心灯可照',当年先师说,只要心里记挂着,再远的路都不算远。“
方荡指尖拂过那行小字,忽然想起长乐编书时,总在深夜对着油灯呢喃:“这样,那些见不到面的人,也能借着药方说句保重。“
老妪临走前,将医书留在了酒楼,说是“物归原主“。方荡翻开时,掉出张夹着的药方,是长乐的笔迹:“桂花三钱,玉兰半朵,明月一盏,煎作相思汤,温服,可抵岁月长。“
冬月初雪那天,酒楼来了位特殊的客人。那是个瞎眼的琴师,抱着琵琶坐在角落,指尖在弦上摸索着调弦。酒客们嫌他扰了兴致,掌柜正要上前劝说,方荡却拦住了:“让他弹吧,我来填首词配他的曲。“
琴师的弦音有些涩,却带着股执拗的清亮。方荡提笔写下《听雪词》,写的是“盲眼人听雪落,心有明月自澄明“。琴师弹到动情处,忽然停了手,朝着方荡的方向拱手:“先生的词里,有槐花的香气。“
方荡心头一震。那是他给云南乡村学校捐赠声波设备时,失明小姑娘说过的话。
“二十年前,曾有位女先生教过我,“琴师摩挲着琴弦,“她说声音能画花,能描月。她送我的琵琶上,刻着朵槐花。“他摘下琵琶背面的木牌,上面果然刻着小小的槐花,纹路里还留着淡淡的红漆——那是长乐晚年走江湖时,总在随身物件上漆的颜色。
那天雪下得很大,琴师弹了整夜,方荡填了整夜的词。弦音与墨迹交织,像场跨越时空的对谈。天亮时琴师离去,留下那把琵琶,说“该还给懂它的人“。方荡抱着琵琶,忽然想起长乐总说要学琴,“等你不忙了,我们就一个弹一个唱“,原来她真的把这份念想,种在了别人的生命里。
开春后,杏花楼的生意忽然兴旺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听说,这里有位方词客,写的词能解相思,能慰乡愁。有人揣着他的词千里寻亲,有人对着词句哭湿了枕头,还有痴情的姑娘,把他写的《重逢令》绣在帕子上,日日带在身边。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镜
- 66958字07-23
- 帝无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南华无忧)的经典小说:《帝无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1014148字07-15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
- 开天辟地见苍凉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佚81194)的经典小说:《开天辟地见苍凉》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4582058字07-15
- 风起宁古塔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浪子边城)的经典小说:《风起宁古塔》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680191字07-24
- 三国:不装了,我是霸王项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今日爆更)的经典小说:《三国:不装了,我是霸王项羽》最新章...
- 389587字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