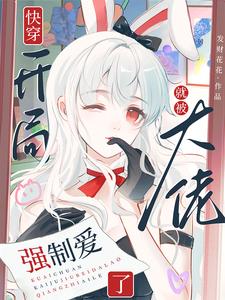第280章 因为我《石峡遗址发掘报告》的编写提前了
3年底至1978年底经过三次发掘,揭露面积3666平方米,清理不同时期墓葬座。发现灰坑、柱洞、灶坑、红烧土、房基等文化遗存,为研究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内涵、特征、年代、分期及与其他有关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典型实物资料。同时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峡文化与长江中下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吸收遗留下痕迹。但是这些重大意义,不能光靠我们说,必须要有发掘报告出来,以前是没有条件,现在改放了,这事也是时候提上日程了。”
说到这,杨先生笑了,“其实这事也怪你,之前你在河宕遗址参与编写资料,让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编写大大加快进度。这样一来,就刺激到石峡遗址工作组了,甚至省博领导觉得河宕遗址这么晚发掘,报告都快要编写出来了,石峡遗址这么重大的遗址,发掘这么多年,报告的进度却比河宕遗址还晚,这不应该。”
“而且,你之前的河宕遗址的表现得到王局长以及省管委会相关领导的一只肯定,因此,领导们也想让我们的发掘成果早点展示出来。”
敢情是自己的乱入,改变了历史走向。
这也是好事。
虽然有领导好大喜功的元素。
但,这真是好事。
一般来说,一个遗址的发掘到发掘报告出来经历的时间周期,大部分都是十年起步。
甚至更久的,几十年没出来也正常。
就算是建国后第一部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白沙宋墓》也从发掘到出版差不多也要6年的时间。
当然编写跟出版不是一回事。
比如后世侯灿先生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从编写完成到出版,中间就间隔了35年。一直到侯先生去世,机缘巧合之下,才能出版。
但不管如何,石峡遗址的报告编写工作进度提前这么早,都是一件好事。
这样一来,杨先生就要带他去认识朱非素先生了。
朱非素先生是北考古大61届毕业生,跟北大李伯谦先生是同班同学,比杨先生晚三届,是省博考古队为数不多的女先生之一。
她跟杨先生跟熟悉,两人既是北大的师兄妹,又是同一个工作队的同事。
因此在石峡遗址发掘过程中,多有合作,甚至,发掘报告两人也有分工合作。
之前苏亦在省博实习,朱先生在石峡工地,这一次,苏亦才有机会拜访对方。
朱先生的经历非常传奇。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2页 / 共14页
相关小说
- 亲爱的,请把钢笔还我,好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给我来杯热可可)的经典小说:《亲爱的,请把钢笔还我,好吗?...
- 1335894字04-12
- 穿六零,进兵团,拿下禁欲兵哥哥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爱吃蔓越莓花生的顾暖)的经典小说:《穿六零,进兵团,拿下禁...
- 1181024字05-02
- 下山被未婚妻背刺,我成神医后她又后悔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江裔)的经典小说:《下山被未婚妻背刺,我成神医后她又后悔了...
- 584344字04-28
- 快穿:开局就被大佬强制爱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发财花花)的经典小说:《快穿:开局就被大佬强制爱了》最新...
- 566928字05-03
- 星芒璀璨:庶女的华丽逆袭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小宝儿Vanessa)的经典小说:《星芒璀璨:庶女的华丽逆袭》最...
- 1221636字04-02
- 前妻痴情白月光,我找青梅她急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铜锣湾把头)的经典小说:《前妻痴情白月光,我找青梅她急了》...
- 773534字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