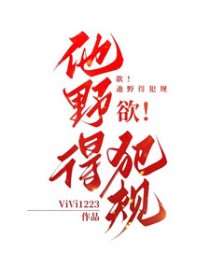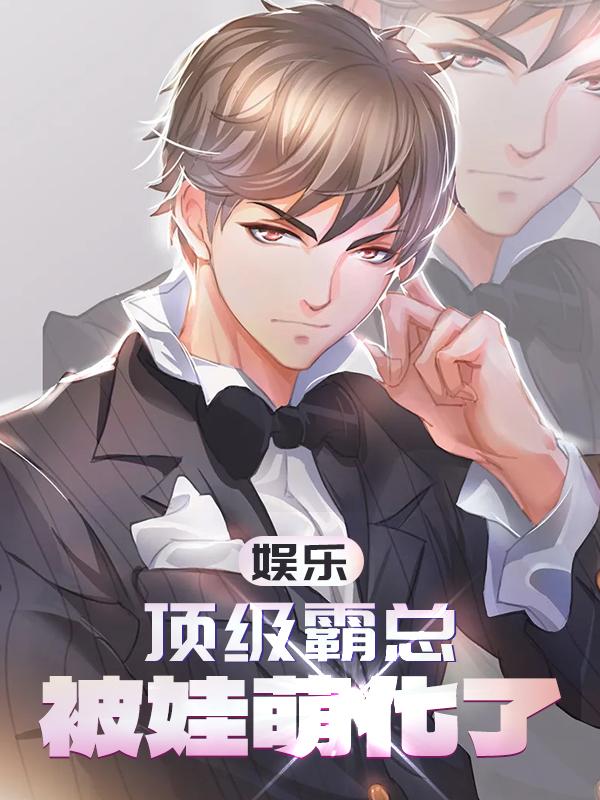第274章 古文字学界大型追星现场
温和的长者形象。
然而,真以为张先生拍脑袋,就以为他记忆力差,那就大错特错了。
于省吾先生就说过,他一生只遇到两个博闻强识、过目不忘的人,其中一位就是张先生,另一位是东北师大的历史学家陈连庆先生。
实际上,不仅于老钦佩张先生。
学界对张先生的认可度也极高。
杨向奎先生曾对听他讲课的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先生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
有种说法,张先生是社科院除了钱钟书先生外,最有学问的人。
能够跟钱钟书先生齐名,就知道张先生的学问之大。
大学问家写的文章,苏亦听不懂,也是正常的。
看着张先生在会场中,用着一口带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讲述着他的文章,苏亦只能感慨,传闻是真的,张先生的学问就是大。
当然,张先生在会场上做学术报告的方式也让苏亦印象深刻。
他不仅准备了铭文拓片,还直接拿了一本段注《说文》(《说文解字注》作者:段玉裁)就跟参会的学者讨论中山墓葬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
那么厚的一本书,老先生随身携带,可想而知治学态度之严谨。
他从段注《说文》引出中山王厝鼎铭文中的最后一句“毋替厥邦”的“替”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异常精彩。
至少,不懂铭文,也能够听得懂他在讲述什么内容。
要不是他用段注举例子,苏亦怎么可能会联想到,这个由一高一低两个“立”组成的字,并不是“并”字而是“替”字的初文。
这种从汉字词源做学问的方式,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那么张政烺先生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自然是对的
他这个考释,也被后来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再次证明是对的。
然而,张政烺先生的考证,花费的笔墨却不多,也不过百来个字,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而且老先生肚子里面的墨水太多了,作报告,就喜欢举列子。
还是很贴近生活的大白话。
比如,他讲中山三器中的“圆壶”时,就直接评论说,“这篇铭文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多是空话套话,就像解放前他家乡山东荣成一带土财主出殡时的‘辞灵告文’。”
生怕大家听不懂,他补充说明。
“我们山东的这些土财主,实在无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4页 / 共15页
相关小说
- 欲!他野得犯规
- 欲!他野得犯规章节目录,提供欲!他野得犯规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856913字07-22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627559字07-06
- 重生八零,反派老公爆宠我
- 710476字07-22
- 我不想当巨星
- 我不想当巨星章节目录,提供我不想当巨星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2971034字07-22
- 娱乐:顶级霸总,被娃萌化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墨者0)的经典小说:《娱乐:顶级霸总,被娃萌化了》最新章节...
- 2323430字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