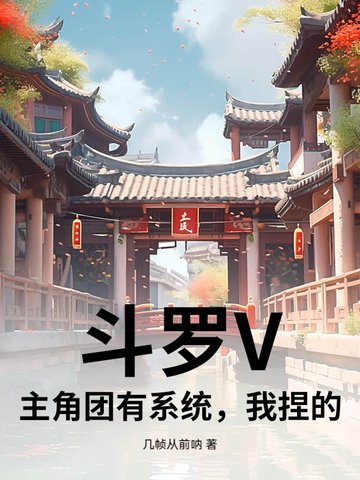第100章 朱见沥的《防灾救灾八策》
“上头?哪个上头?”于谦追问。
“这个嘛……”班头支支吾吾,“自然是……管粮仓的刘书办,管赈济的王典史……都是按规矩办事!”
朱见沥明白了,这“剥洋葱”剥到这里,露出的全是些屁大点的小吏。
可这些人就像一群饿疯了的耗子,在朝廷赈灾的这艘大船底下疯狂打洞,啃噬着船板,也啃噬着灾民最后一点希望。
接下来的几天,朱见沥坚持深入灾民窝棚区。
所见所闻,让他那本麻纸本上,又添了血淋淋的几笔:
“义仓”变“鼠仓”: 打着“救灾”旗号的义仓,管理权牢牢把持在乡绅和胥吏手中。
灾民想借粮,行!借一斗,秋后还三斗,还得搭上家里唯一值点钱的破锅或几间房契当抵押。
朱见沥亲眼看见一个老农捧着空空的“借粮契”欲哭无泪,嘟囔着:“这哪是借粮,这是卖命啊!”
汤杰气得直哼哼:“这他娘比放印子钱的还狠!”
“以工代赈”变“无偿徭役”: 官府征发灾民修水渠,美其名曰“以工代赈”。
结果呢?说好的“日给米半升”成了空头支票,监工的小吏不仅克扣工钱,还动辄打骂。
灾民们累死累活,只换来一句“朝廷恩典,管你们饭就不错了!”
朱见沥看到那些在烈日下挥汗如雨、骨瘦如柴的民夫,再看看远处树荫下摇着扇子喝茶打屁的监工小吏,气得小脸通红。
于谦则冷冷道:“此非赈灾,乃役民如牛马,其心可诛,其行可杀!”
“皇恩浩荡”变“层层扒皮”: 朝廷拨下的救灾银两和粮草,经过省、府、州、县各级官吏的手,如同进了筛子,层层漏,层层刮。
到了灾民手里,可能只剩下一把发霉的陈米或几尺破烂布头。
一个落魄的老秀才悲愤地对朱见沥说:“小公子,您知道吗?这救灾粮啊,从京城出来是白面,到了省里变糙米,到了府里变杂粮,到了县里……就变成喂牲口的麸糠了!还美其名曰‘节省开支,惠及更多’!”
朱见沥听得直发懵,这“惠及更多”的逻辑,比汤杰的刀法还让他难以理解。
这日傍晚,一行人抵达了榆林镇卫所。
榆林卫的一个副千户和本地知县早已得到消息(汤杰的亲兵提前通报了身份,但没敢说吴王),屁颠屁颠地跑来“接风洗尘”。
驿站正堂,灯火通明,一张大圆桌上摆满了鸡鸭鱼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我的修仙模拟器
- 214890字07-30
- 以禁忌之名,贯彻万古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君渊yo)的经典小说:《以禁忌之名,贯彻万古》最新章节全文阅...
- 649513字03-13
- 世子凶猛:这个小娘子,我抢定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月下果子酒)的经典小说:《世子凶猛:这个小娘子,我抢定了》...
- 2516618字06-25
- 东京人不讲武德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墨斩黑天)的经典小说:《东京人不讲武德》最新章节全文阅...
- 1519052字06-24
- 凡人流:参天窃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观纶)的经典小说:《凡人流:参天窃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50556字07-17
- 斗罗V:主角团有系统,我捏的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几帧从前呐)的经典小说:《斗罗V:主角团有系统,我捏的》最...
- 546973字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