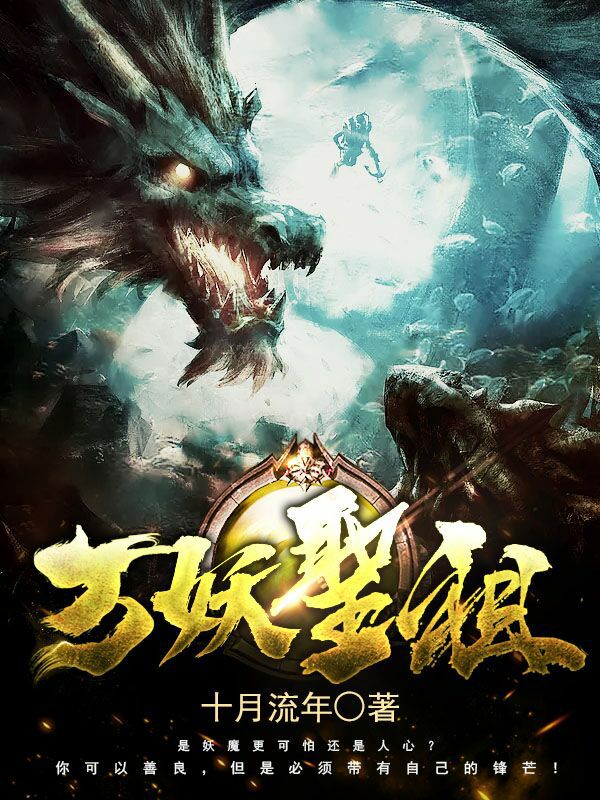五九九 一剑之决(二)
摇头,“可若我便是无可证明呢?这世间本就没有自证子虚乌有之事的道理,倘若疾泉今日还在,他应该也想明白了,或许能帮我澄清这事,只是我——实在不似他那般能言善道。”
他看起来有点黯然:“他倒是好了,随随便便一句话,自己走了,留下我不晓得怎么解释好。”却也还是解释道:“他那时认为我是所谓‘神秘人,是从拓跋对‘神秘人之态度推断而得。拓跋的确一直以为,那个接近他、不断游说他的人正是我,只是因种种缘由彼此不曾说穿。”他细述了一番推测的细节,末了:“这所谓‘神秘人,精通易容之术,又极擅钻弄人与人之间那么一丝相互猜疑之缝隙,手段老辣,以至于——就连疾泉这样的人都栽了跟头。你心中有疑不奇,今天这般来找我对质倒是好事,只因——若你不来,说不定你我之间这缝隙,又要被他给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