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千二百六十四章
且代价严重。例如,在美国,60%以上的校园枪击案和四分之一以上的炸弹案件都牵涉到复仇的渴望。虽然很少有人会公开承认赞成复仇,但人们显然喜欢听复仇的故事。
早期的哲学家更关注美德,认为复仇是一种非常消极的现象,仿佛代表着破坏性和反社会;但复仇不只有丑陋的那一面。
在中国早期史诗中,家庭与民族并不对立,家庭被视为氏族关系的延伸和扩展。中国的鬼灵复仇的来源是原始人的血族复仇和祖先崇拜,也是后者的变形及多样化延展。从中国古代复仇文化形成的原生态看,血族复仇将人类潜伏的原始攻击本能充分地宣泄出来,加以固化和强化,建构并增强了原始人个体与其族属整体的关系,成为早期集团必不可少的凝聚力。因此,在人类许多民族中,都存在着强大的复仇情结,成为一种时时浮现、恒久而稳定的集体无意识。
从血族复仇直接功能来看,其强固了华夏之邦的祖先崇拜,后者作为基础的鬼灵信仰又充分吸收了复仇的正义理性精神,将复仇理解解释为正义的实现,为此,鬼灵显圣成为正义实现的合理形式之一,在流传的漫长过程中大量掺入现实生活感知经验,愈加花样繁多。作为血族复仇遗传的血亲复仇,在古代中国社会伦理化规范的倡扬下,借重鬼灵复仇方式的必然性和超时空性,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理想化的人生图景和情感归宿。于是,带有了极为活跃的文学因子,想象世界中的鬼灵报怨作为现实中难于复仇的补偿,而持久地占据着文学题材和主题的一个重要分支。甚至,带着这一崇尚正义复仇的有色眼镜,古代中原人也容易更为关注周边民族的相关习俗。
而儒家思想对复仇文化也起了巨大作用。孔子提倡的以直报怨的意义已不在于个体为一家一族之恨平不平,而干涉到社会公理的伸张,有儆世诫恶之效。其对恶行发出者自身产生立竿见影作用,更有震撼人心的新闻效果。中庸准则的提倡,与孔子倡扬的复仇观也是不相违背的。程子《中庸题解》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天下之定理。”正道正理,愈加佐证了正义复仇定则的不可移易,仁的具体实施恰在其中。
“礼”字说到底为的是调适群体内部关系。而复仇对于氏族群体的凝聚作用,原始人早就意识到了,在共同面对仇敌的大旗号令下,一切嘈杂之音都可以被正义呼喊所淹没。然而只是到了先秦儒家这里,才开始突出正义实施的理性庄严,这当然不限于复仇。“学仁,不让于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6页
相关小说
- 帝后成长计划
- 989088字04-21
- 明星前女友报复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鸥问我)的经典小说:《明星前女友报复我》最新章节全文阅...
- 1890670字06-07
- 百无一用的小师妹[NPH]
- 287468字10-20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
- 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章节目录,提供举案齐眉,终是意难平(快穿)的最新更新...
- 1201425字10-19
- 火影:过客与归人
- 火影:过客与归人是由作者木逸空著,免费提供火影:过客与归人最新清爽干净的文字章...
- 1602071字06-14
- 宝可梦之龙柱力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月照大地)的经典小说:《宝可梦之龙柱力》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745677字1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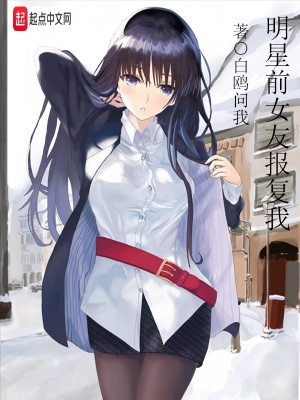
![百无一用的小师妹[NPH]](http://www.qibaxs7.com/files/article/image/0/110/110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