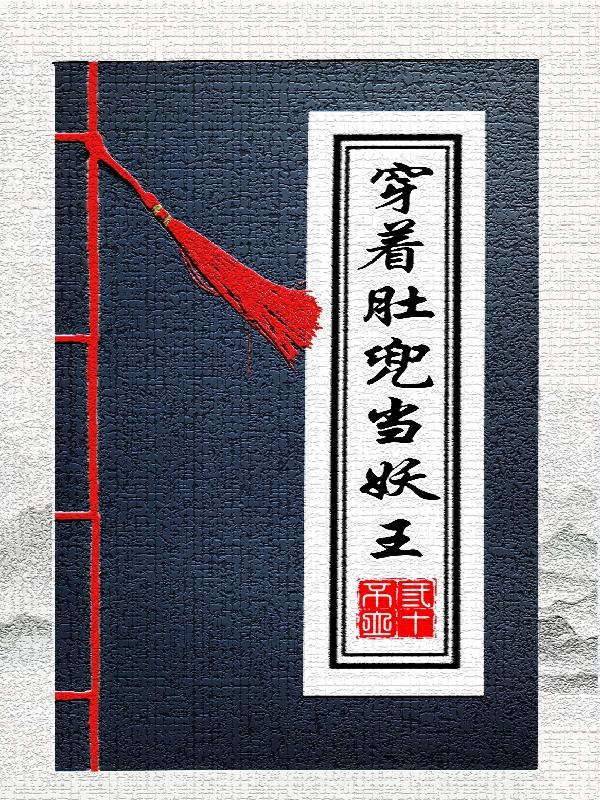第186章 孤,做你的山
>
有啊。
怎会没有。
可她说,“大人如昭昭日月,奴是阘茸浊流,思来想去,不敢攀附。”
这尊卑贵贱,早就看得分明,因而在今日说出口来,温和坦荡,没有什么赌气的心思。
可那人说,“阿磐,你亦是昭昭日月。”
阿磐浅笑,不去驳他。
随他怎么说,怎么说都好。
待她好时,她便如昭昭日月。
待她不好,她就是阘茸浊流。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早看了个清楚明白。
他们轻声细语地说话,在这晋阳的民宅里,不疾不徐,不急不躁。
那人问,“从前可有人提起你父亲的事?”
她微微摇头,“不曾。”
“你父亲是晋国公卿之子,出生即被选中,悉心培养,年有十五,送往中山。那是顶级的细作,潜伏于怀王身边,不及而立,便做了中山的公侯。”
哦,难怪她记得曾居于那样一处奢华宽阔的高门府邸。
也难怪当初萧延年要说,“没有你父亲,中山也不会亡。”
一时有些失神,听那人又道,“因而孤娶与不娶,你都是公侯贵女。”
阿磐心里缓缓一舒,若是如此,那便再不必因了出身而轻贱了自己。
不管在晋国,还是在中山,她不都是公侯之女吗?
那人的下颌不知何时冒出了些许的胡渣,扎得她脖颈麻麻痒痒的,听那人又道,“孤做你与阿砚的山。”
王父是山,能护佑她们母子,阿磐知道。
然而做了她与阿砚的山,难道就不会再做云姜与那个孩子的山了吗?
谢玄有没有碰过云姜,那个孩子姓谢还是萧,他大抵心里是有数的。
可既还留着她们母子在东壁,也定有他们的缘由。
旁人都不提云姜,她便也不好去提。提了好似就是生妒,不提好像这个人就不曾有过,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一样。
阿磐轻声,“大人能做到哪里,便做到哪里,不管什么时候,阿磐都不会苛求大人。”
不管算不算以退为进,话说到这里,不求便是求了。
那人蹭着她的脸,“孤再不疑你,亦不问你的过去。赵国大局一定,就带你们母子回家。”
有家是好事,便是她不要,阿砚也总得归入谢氏宗庙。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沐家小辣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萌小兔不萌)的经典小说:《沐家小辣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580127字10-06
- 阅她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珍珠发卡)的经典小说:《阅她》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
- 465178字12-14
- 我家水缸古通今囤货娇养病娇王爷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念清梧)的经典小说:《我家水缸古通今囤货娇养病娇王爷》最...
- 495828字12-23
- 穿着肚兜当妖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三十不立)的经典小说:《穿着肚兜当妖王》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894018字12-23
- 黑欲人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琅琊刀客)的经典小说:《黑欲人生》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2697176字12-12
- 综影视之武力值超高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碳烤兔爪)的经典小说:《综影视之武力值超高》最新章节全文...
- 1046983字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