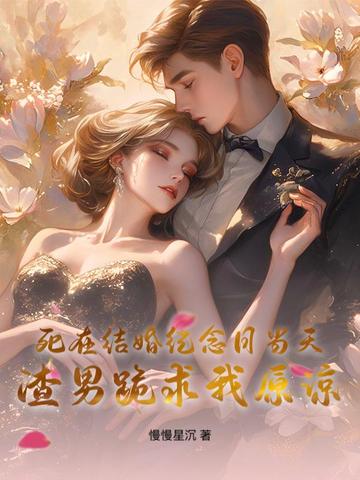第二百零三章 河东盐池的症结
臣的争端,是因何而起?”
拓跋晃不假思索,一口道出:“争执之由,皆因榷税之议。故而,我依姑姑高见,削减了百姓一分税赋,欲以此彰显我朝仁德之风。然而,世事难料,百姓之心非我所愿,此番善举非但未赢得民心,恐怕还会成为那些人攻讦我的理由。”
说着,拓跋晃唇角勾起一抹苦笑。
“实则,你自始至终皆陷于被动之地,”拓跋月温言道,“阿晃,你可曾细思?为何要应对那些朝臣抛来的难题?”
话说至此,拓跋晃若再不明白,也未免太愚钝了。
只见他眸光一亮,缓缓言道:“我明白姑姑的意思了。不论朝臣如何非议,百姓怎样言说,我皆不为所动。河东盐池的症结,不在榷税之上,而在于根治水患。”
闻言,拓跋月未发一语,只含笑望着拓跋晃,一副欣慰至极、孺子可教之态。
拓跋晃忙对拓跋月施了一礼,道:“阿晃受教了。”
他微微蹙眉,沉思片刻后,缓缓开口:“这根治水患之事,前人亦多有试验。忆及三国之时,河东之地,官民一心,于洮河中上游修筑沙渠河,施展了一出‘釜底抽薪’的妙计。他们开凿了沙渠河,令洮水在闻喜县河底镇转向,由南面改道西北,再穿越鸣条岗,最终抵达吕庄汇入涑水。”(1)
以人工之渠,将洮水引走,此法甚妙。
至于大魏,那沙渠河周遭多有淤浅,防汛之力遽然下降。为此,河东官府曾多次征调民夫,对其进行疏浚。
然而,一旦洪水肆虐,情势危急,那沙渠河亦难敷所需。
念及此,拓跋晃不由嗟叹:“不知,官吏百姓会想出什么法子,此乃未知之数。”
“此事不必过虑,”拓跋月悠然道,“你只管将招募治水之策的布告张贴出去,自会有人献计献策。切记,奖赏须丰厚,方能如古之‘移木立信’,激励人心。”
人心一被激励,必对太子歌功颂德。
到了那时,倘若有人再提免税之事,自然就不合时宜了。
拓跋晃将这番话铭记于心,一时间愁容尽消,这才让太子妃郁久闾恩,带着儿子拓跋浚,一道来陪侍。
拓跋浚这孩子,生于太平真君元年六月,自幼便聪慧过人,异乎寻常。
故而,拓跋浚极受祖父拓跋焘的宠爱,时常令其伴在身侧,大有躬亲抚养之势。拓跋浚也由此得了“世嫡皇孙”的美称。
奈何,拓跋浚每被召唤到祖父跟前,太子妃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627559字07-06
- 安贵从容
- 1362288字07-12
- 夫人出逃金丝笼,督军下跪求回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栗子双响炮)的经典小说:《夫人出逃金丝笼,督军下跪求回头》...
- 277282字07-15
- 死在结婚纪念日当天,渣男跪求我原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慢慢星沉)的经典小说:《死在结婚纪念日当天,渣男跪求我原谅...
- 296978字07-15
- 霁月难逢
- 534385字09-09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