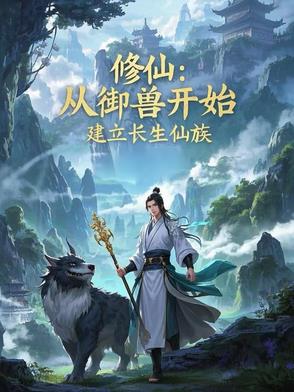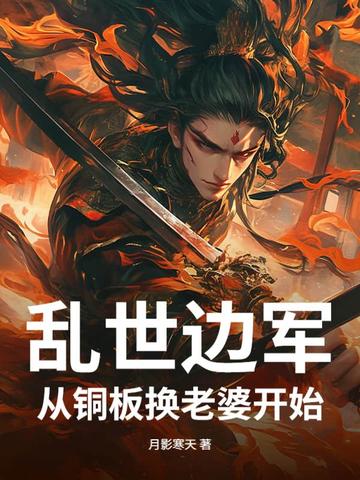第122章 感知融贯佛道智,启智立世制混乱
之否定”的螺旋上升逻辑。“道”的“有无”相生,通过不断打破“有”的固化形态回归“无”的混沌,再从混沌中孕育新的“有”;“佛”的“觉明”识种,则在对“明白”的执着与消解中,不断重组认知的边界。二者都揭示出:真正的创造不是无中生有的魔法,而是对既有存在的持续解构与重构。
当我们将视角拉回现实,这种古老智慧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现代物理学中的弦理论认为,宇宙万物皆由微小弦的振动构成,不同振动模式形成不同物质形态;神经科学揭示,人类的认知世界本质上是大脑对感官信号的重构。这些发现与“晃在”的动态生成、“觉明”的识种构建不谋而合,印证着东方哲学对存在本质的超前理解。或许,道与佛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哲学思辨,更是一种超越二元对立、拥抱流动与变化的生存智慧——在“有无”的摇摆与“明白”的更迭中,我们既是世界的观察者,也是宇宙持续创造的参与者。
从宇宙观层面来看,道家的“道”是一种去中心化、非人格化的宇宙本源。它摒弃了神创论的意志干预,以“道法自然”的理念将宇宙运行归结为一种自发、自洽的秩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描述的,并非线性的时间序列,而是万物从混沌到有序的涌现过程。这种宇宙观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将个体置于与万物平等共生的生态链条中,暗含着现代生态学“万物互联”的思想,我把这种链接用“感知”代替是为了疏通当代的混乱。相比之下,佛教以“缘起性空”解构实体化的宇宙观,认为一切存在皆由因缘和合而生,并无独立自存的本质,然能够支撑种种缘起的根本却是“性空”的。将宇宙视为一个无始无终、相互依存的“性空”网络如是呈现,我把此“性空”理解为“感知”是能让人们进入当代语境。它们的认知不仅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更挑战了人类对确定性的本能追求,展现出超越时空局限的思维张力。
从道的物质哲学纬度,佛的生命哲学维度我们去思维,它们在哲学领悟直达本质的论述已至无上,展现出惊人的深邃,后来者望尘莫及,很难达到这种无上,幸亏有《道德经》和《楞严经》存世,实乃中华之福,世界之福。庄子笔下“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实质是通过消解自我中心的认知局限,融入宇宙大化的流动之中。这种生命观突破了生死的二元对立,将个体生命视为“道”的短暂显化,在“方生方死”的流转中实现精神的不朽。佛教则以“轮回”与“涅盘”构建起独特的生命叙事,认为众生因无明造业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修仙:从御兽开始,建立长生仙族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在下傲天)的经典小说:《修仙:从御兽开始,建立长生仙族》最...
- 1121880字07-05
- 神秘先行者
- 3612014字11-23
- 南北无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李还乱)的经典小说:《南北无间》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473480字06-23
- 乱世边军,从铜板换老婆开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月影寒天)的经典小说:《乱世边军,从铜板换老婆开始》最新章...
- 615049字06-25
- 苦刀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陈年苦瓜)的经典小说:《苦刀》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
- 805821字04-17
- 七零年代,退伍糙汉被我带飞暴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七初九)的经典小说:《七零年代,退伍糙汉被我带飞暴富》最新...
- 943355字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