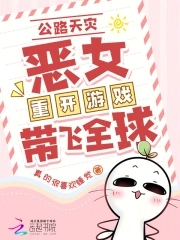第五章 襄樊之战:宋元交锋,战略要冲
宋史·度宗本纪》)。贾似道被迫“自请督师”,却仅派范文虎率十万大军“象征性救援”,结果“舟师至鹿门,遇元军,全军覆没”(《宋史·范文虎传》)。至此,南宋“长江防线”名存实亡,元军“沿汉水直下鄂州,顺江东进”(《元史·伯颜传》)的通道彻底打通。
第三章 胜负之钥:战略、技术与人心的三重博弈
3.1 元军的“技术革命”:回回炮与水陆协同
襄樊之战中,元军的“回回炮”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种源自阿拉伯的抛石机,经蒙古工匠改良后,“机发时声如雷霆,所击辄糜碎”(《黑鞑事略》)。襄阳城楼“厚五丈,高十丈”(《襄阳府志》),却“为回回炮所中,石入城,穿穴透壁”(《元史·阿术传》)。守军“以木栅蔽之,栅破则人亡”(《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最终“城不可守”。
水陆协同战术的运用,同样是元军获胜的关键。元军控制汉水后,“以战船五百艘,列于江面,昼夜巡逻”(《元史·阿术传》),切断了襄阳的粮道;又派骑兵“沿汉水两岸,驰骋示威”(《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制造心理压力。这种“陆攻城、水断粮”的立体攻势,让襄阳守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最终崩溃。
3.2 南宋的“体制性溃败”:党争、腐败与战略误判
襄樊之战的失败,根源在于南宋的“体制性腐败”。贾似道专权,“凡台谏弹劾,非其私党不问”(《宋史·贾似道传》),导致“边将无权,朝廷无策”。吕氏家族虽“世守荆襄”,却“自擅兵赋,不输朝廷”(《续资治通鉴长编》),朝廷对其既依赖又猜忌,战时无法有效调度援军。
更致命的是战略误判。南宋君臣迷信“长江天险”,认为“襄樊虽失,犹有长江”(《宋季三朝政要》),未及时加强两淮防线。直至元军“顺江东下”,宋廷才“仓促应战”,结果“江防未固,舟师不精”(《元史·伯颜传》),最终“临安失守,崖山败亡”(《宋史·瀛国公本纪》)。
3.3 人心向背:守将的忠诚与绝望
吕文焕的“坚守与动摇”,折射出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前六年,他“竭力拒守”,甚至杀退元军多次劝降;但樊城陷落后,目睹“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襄阳守城录》),他最终选择投降。这种转变,并非单纯的“贪生怕死”,而是“忠君思想”与“现实绝望”的冲突结果。
普通百姓的苦难更令人唏嘘。战乱中,襄樊“父子相食,夫妇离散”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5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智械之后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夏玉月)的经典小说:《智械之后》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830855字10-28
- 译电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青灯轻剑斩黄泉)的经典小说:《译电者》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2328375字07-26
- 全民公路求生:欧皇重开带飞全球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真的很喜欢睡觉)的经典小说:《全民公路求生:欧皇重开带飞...
- 693959字07-30
- 归墟
- 42957字06-28
- 开局一辆购物车发育全靠卡BUG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凤今天不想码字)的经典小说:《开局一辆购物车发育全靠卡B...
- 994528字10-01
- 黑暗本源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番石榴爵)的经典小说:《黑暗本源》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485452字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