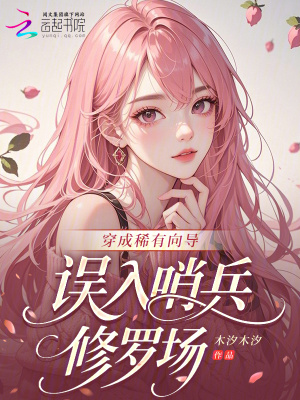第二章 蒙古灭西夏:兵锋所指,国破城亡
西夏灭亡后,蒙古彻底打通了“蒙古高原—河西走廊—中亚”的通道。1235年,拔都率蒙古第二次西征(长子西征),正是以西夏故地为跳板,直抵多瑙河流域。西夏的灭亡,标志着蒙古“先弱后强”战略的成功——先灭西夏、西辽,再灭金国、南宋,最终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国”。
(二)文明的劫难与遗存
西夏的灭亡,是一场文明的浩劫。《西夏实录》载:“中兴府破,大夏文物,尽入于火;佛寺、道观,皆成焦土。”西夏文字(曾通行于西北200年)、西夏佛经(如《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西夏官印(如“首领之印”),均因战乱大量散佚。直到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发现,才让世人得以窥见西夏文明的真容——出土的10万余件文物中,包括西夏文佛经、世俗文献、绘画与丝织品,被誉为“打开西夏之门的钥匙”(王国维语)。
(三)后世的评价与反思
对于西夏灭亡,元代史家《宋史·夏国传》仅用“夏自景宗元昊称帝,传十主,凡一百九十年,为蒙古所灭”寥寥数语概括,隐含着“蛮夷政权终为大邦所并”的传统史观。现代学者则更注重从文明冲突的角度分析:西夏作为“河西走廊的多元文化政权”,其灭亡本质上是“封闭的边疆政权难以抵御游牧-农耕复合帝国的冲击”(陈寅恪语)。这种冲击,既是军事的,也是文化的——蒙古的征服,最终将西夏纳入了“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的体系,西北边疆的民族融合由此加速。
五、贺兰山的挽歌
当蒙古铁骑踏碎中兴府的最后一堵城墙时,贺兰山的雪依旧覆盖着西夏王陵的夯土台基。那些刻着西夏文的碑碣、绘着飞天的壁画、铸造着“大夏通宝”的钱范,都在风沙中沉默。一个王朝的终结,不仅是疆域的消失,更是一段独特文明的谢幕——它曾在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夹缝中绽放,用党项人的智慧与血汗,在西北大地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歇。西夏的灭亡,印证了一个永恒的规律:在冷兵器时代,封闭的政权难以抵御游牧帝国的冲击;而那些能够在夹缝中求生的文明,往往需要更开放的胸襟与更坚韧的韧性。贺兰山的雪会融化,黄河的水会奔涌,但西夏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它是悲剧,更是警示;是终点,更是起点。
喜欢一本书带你读懂中国史请大家收藏:(www.qibaxs10.cc)一本书带你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6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网游之九转轮回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莫若梦兮)的经典小说:《网游之九转轮回》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21899938字07-14
- 智械之后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夏玉月)的经典小说:《智械之后》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830855字10-28
- 译电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青灯轻剑斩黄泉)的经典小说:《译电者》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2328375字07-26
- 开局一辆购物车发育全靠卡BUG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凤今天不想码字)的经典小说:《开局一辆购物车发育全靠卡B...
- 994528字10-01
- 黑暗本源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番石榴爵)的经典小说:《黑暗本源》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485452字06-26
- 穿成稀有向导,误入哨兵修罗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木汐木汐)的经典小说:《穿成稀有向导,误入哨兵修罗场》最新...
- 318250字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