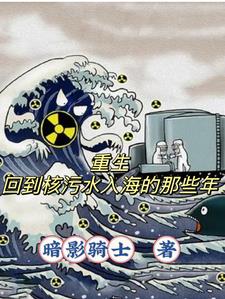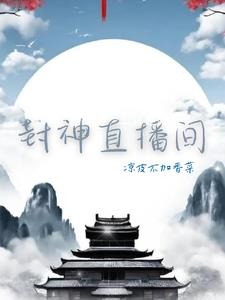第二十三章 辛弃疾壮志难酬:豪放词章 爱国情怀
被任命为滁州知州。当时的滁州因战争破坏,“城郭皆废,居民不满百家”(《宋会要辑稿·食货》)。辛弃疾到任后,“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宋史·辛弃疾传》),仅用一年时间便“荒陋之气,一洗而空”(周密《齐东野语》)。
此后,他历任江西提点刑狱(1172年)、湖北转运副使(1175年)、湖南安抚使(1179年)等职,每到一处都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在江西,他镇压茶商叛乱,“募兵分捕,旬日间尽擒之”(《宋史》);在湖南,他创建“飞虎军”(一支两万人的精锐部队),“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兵志》);在福建,他整顿海防,“增置战船,教习水战”(《八闽通志》)。
但这些政绩并未为他赢得政治资本,反而加深了他的孤独。主和派官员攻击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宋会要辑稿·职官》);宋孝宗虽认可他的能力,却始终将其视为“能吏”而非“帅才”。1181年,四十二岁的辛弃疾因“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遭弹劾,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闲居生涯(1181—1203),先后寓居上饶带湖、铅山瓢泉。
三、词章寄志:豪放词风中的“英雄失路”之痛
3.1 豪放词的“破”与“立”:从婉约到英雄之词
辛弃疾的闲居生涯,反而成就了他词作的巅峰。此前,宋词以柳永、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为主流,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离愁别绪。辛弃疾则以“以文为词”的创新,将家国之痛、英雄之悲注入词中,开创了“豪放派”的新境界。
他的豪放,不是简单的“大声镗鞳”,而是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悲剧熔铸于具体意象。例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醉里挑灯看剑”一句,通过“醉里”“挑灯”“看剑”三个细节,将英雄迟暮的无奈与对战场的渴望浓缩在七个字里;“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则以夸张的数字(八百里指牛,出自《世说新语》)渲染军营的热烈,与“可怜白发生”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
这种“以乐景写哀”的手法,正是辛弃疾的独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所谓“豪”,不仅是气势的宏大,更是情感的真挚——他没有刻意回避痛苦,而是将“壮”与“悲”交织,让读者在“金戈铁马”的豪情中感受到“报国无门”的沉郁。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归墟
- 42957字06-28
- 开局一辆购物车发育全靠卡BUG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凤今天不想码字)的经典小说:《开局一辆购物车发育全靠卡B...
- 994528字10-01
- 重生:我回到核污水入海的那些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暗影骑士)的经典小说:《重生:我回到核污水入海的那些年》...
- 522322字09-17
- 封神直播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凉皮不加香菜)的经典小说:《封神直播间》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836656字12-22
- 闪点计划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约翰尼阿芳)的经典小说:《闪点计划》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1724738字06-05
- 网游之天下第一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青面佛)的经典小说:《网游之天下第一》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4736848字07-30